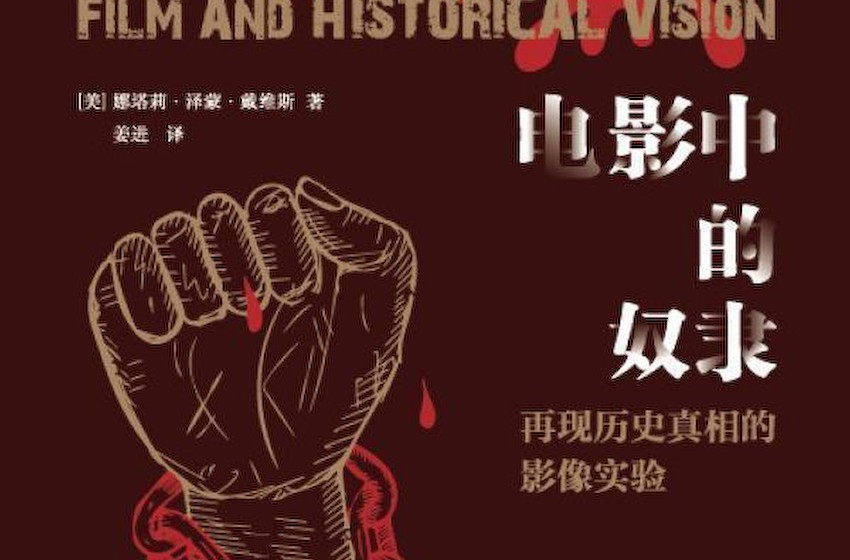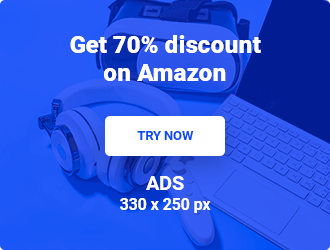乌尔善说《封神第一部》
西方电影里关于西方神话的讲述由来已久,导演乌尔善觉得中国人自己的东方神话也一定需要电影创作者去做——早晚有人去做,只是恰好他一直对此非常着迷,所以他与“封神”互相选择了彼此。
华丽的大场面之下,《封神三部曲》探讨的是当下充满张力的命题:对父权的反叛,对偶像崇拜的粉碎等等,那些关于神与人、成长与觉醒、权力与欲望的交织,都是古老的东方神话和历史故事在当代的表达。
“神话永远是当代的神话,永远是我们当下的观念,是关照我们整个文化发展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的,我想要在这个层面去重新讲述属于我们的心灵故事。”在《封神第一部》上映前二十天,毒眸与乌尔善聊了聊这部会成为他职业生涯关键节点的作品。
上映三天,对于一个耗时十年的神话史诗电影项目来说,或许一切都只是起步阶段。而对导演乌尔善来说,不管什么样的结果,都是他早有准备且必将承受的,因为从最开始他就知道,这是他必须做的电影。
《封神第一部》

以下是经整理后的乌尔善的自述。
必须做《封神三部曲》
拿中国观众能感同身受的中国经典故事,做一个中国的超级大片,没有什么可以参照的例子,中国电影里的中国神话故事很少。像《封神》的故事,它的国民性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每个人一提到“封神”,脑子里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角色认知,很少有中国人说“我不知道封神”。
所以,如果中国要选择一个题材去拍神话史诗,“封神”的故事是唯一选择。它是把明代以前所有的宗教文化、世俗的神话传说,再加上历史的想象,融会贯通写成的非常庞大的文本,拥有神话写作的整个幻想性和隐喻性,里面有真实的历史、时代的变革、善恶的斗争和英雄成功等等,还包含普通老百姓的信仰,这是史诗类型的必须的原则。
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达到一定成熟程度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类型的电影。
神话史诗类型有几次高峰,一个是电影最早期格里菲斯时代,用《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等影片对他们的民族文化历史有非常宏大的表达;二战以后,美国成为西方文化和经济中心,《宾虚》《十诫》《埃及艳后》等大量古希腊罗马宗教故事,是对西方文化整理后电影化的表达;70年代冷战以后,《星球大战》跟美国当时的太空探索形成密切关系,但本质是古希腊神话的变体;现在对娱乐电影影响最大的漫威和DC,完全是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的现代化放到了美国的当代社会的变体中。
《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

可以发现,这个类型(神话史诗)贯穿着任何民族的文化历史,它需要不断地被重塑,不断地被当代化,不断产生跟现在观众交流的可能性。
神话最重要的是建构民族的公共梦境,在这个梦境里面去探讨我们的文化精神、民族情感和价值观,这些东西是特别有意义的,永远应该被一次次地讲述。我做这件事是很有使命感的。
神话史诗类型是对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的总结。中国一直以灿烂的传统文化为自豪,中国的电影创作者一定也会做这种电影,早晚有人去做,恰恰我一直对历史、神话等非常感兴趣。
电影本身的力量和语言、呈现方式,让它成为公共艺术最重要的工具,我选择做电影导演,希望能够找到这种适合电影表达的类型题材,像神话史诗就非常具备电影感,为电影去创造梦境,中国电影也需要一个这样的类型。
《封神演义》已经是一个最著名的故事,三千多年来,从历史变成传说变成神话,我要拍每一个中国人的“公共神话”,这就是最好的题材——电影是在造梦,《封神演义》是全体中国人的公共梦境,为什么不做这个?

难度确实也不小,神话史诗类型需要对传统文化真正有一个梳理、归纳、提炼,还需要好的表达能力,以及电影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重要的时机问题。
十年前,大家对国产片都挺有信心,我之前的导演作品在商业上也还算成功,当时的电影资本也非常活跃,愿意支持这样的项目,毕竟十年八年对投资来说是风险非常大的,但大家都很乐观,于是就这么开始了。我觉得时机也比较合适,我的年龄也比较合适。
2012《画皮Ⅱ》之后,如果再选择奇幻的动作史诗类型,我就希望做一个挑战性最强的,用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它。2014年6月是第一次剧本策划会,我正好42岁,是一个导演能量最旺盛的时期,我想把它全用来拍《封神三部曲》——虽然所有的事情不可能按自己理想的方式发展,但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应该选择一个各方面的难度都最高的电影项目,而不是做一个熟悉的、对我来说容易做的电影。
如何让现在的观众相信这个故事
剧本花了四年的时间,2018年开拍后还在修改,最开始主要是请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做“封神”和商周历史方面的解读。我们找到了很多关于这段历史事件的文本,既有比如《尚书》《史记》《战国策》这种历史文本,还有《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等小说,文本差异很大,每个时代对这个事件的描述都有不同。
像我们改编的两个文本,宋元的《武王伐纣平话》是分上中下三卷的2万多字的话本小说,主要角色也是殷郊和姜子牙,但没有昆仑仙人这套设置,明代的《封神演义》添加进去的大量的道教元素,最终写作目的是给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形成一个神仙谱系,文字成就其实一般,但文化价值非常高,因为高度融合了历史真实、宗教体系还有民间传说,综合性特别强。
任何时代的写作都是当代的,如果我们去根据这些文本拍一个电影,也仍然在寻找它的当代性,这是最重要的。
在今天要上映《封神第一部》,应该传承了原作的哪些元素?改编哪些东西?如何与现在的观众真正产生共鸣?它有什么样的当代价值?当时大量的时间是在做这个工作。
现在观众看到的所有内容是从当代人的角度,对封神演义的文本进行三个很重要的改编后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改编是封神榜的设定,原作里面封神榜是一个死亡名单,人间要发生一场浩劫,这个设定对当代的观众来说,最起码对我来说很难接受,因为我们不太相信“昊天上帝打工”这件事。

所以现在的“封神榜”在电影里是大家都需要的东西,它意味着一种善恶的判断,凝聚着所有人类的魂魄,产生一种超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唯有所有人推崇敬仰的共同领袖(天下共主),才能够调动——这个设定很重要,它相当于给故事一个焦点,大家都要去追随这条线索。
拿着封神榜的姜子牙,要带着观众进入到整个历史事件中去,做出选择:谁是真正的天下共主?把封神榜交给谁?这样故事就拥有了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在这中间,有个很重要的关于人性的探讨主题:到底谁能开封神榜?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为天下苍生的命运而开榜?这是非常根本的改编。
《封神第一部》是纣王无道、诸侯反朝歌,是一个觉醒故事,第二部是保卫家园和英雄成长的故事,第三步才是武王伐纣,然后封神。这是一个非常规整的三段结构,我们变成三部曲也是依据于这个构架。
结构清晰后,就是找到主角。原作里面姬发一直在,但存在感很低,到最后的牧野之战才和纣王碰面,如果电影剧本这么写的话会很难,因为这两个人物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就在考虑,谁来做第一男主角。
一般《封神演义》的故事是拿姜子牙做第一主角,但这不够有戏剧曲线,因为姜子牙是一个成熟的智者,作为主角承担的主题会比较简单,没有一个年轻人所承担的主题那么丰富——史诗一定要承载成长主题,人格碰到什么样的挑战、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然后获得人性成长,这是史诗尤其英雄史诗必须要处理的题材。
《封神第一部》殷寿

从英雄史诗的角度来说,唯有姬发可以做男一号,故事一定要从他开始,反派的男一号一定是殷寿,因为在剧作上需要他们两个人之间形成非常紧密的关系,一个偶像和粉丝的关系。所以我们最大的改编除了封神榜的设定就是姬发,他成了从小跟着殷寿长大的质子,还崇拜殷寿,想成为像殷寿那样的英雄,他要通过一些事件才能觉醒,这是第一部要讲的主题。
第二部他会面对强大的挑战,要去保护自己的家园,开始进一步地成长,所以这个设定是特别关键的,把两个最核心的人物关系先建立得很牢固,这样整个戏剧性会比较强烈——从崇拜纣王到发现他的真相,然后反叛,成为他最重要的对抗者,最终战胜他。
这些改编需要做很多背景的调查梳理,要把所有东西都了解清晰之后,忘掉它们。剧作阶段要忘掉那些在电影化处理以后的奇观,这些东西在剧本创作初期都没有意义。
一定要用最简单的方法去思考这个题材。如果要用很低的成本拍这个故事,哪些剧情是不可以被舍弃的?如果要用艺术电影的方式或者是一个舞台来呈现这个故事,哪一条叙事线是一定不能被删减的?哪种情感是最打动人的……需要我们特别客观地去判断这个东西。
我想了挺长时间,如果让我保留最不可以被删除的人物和事件的话,可能是文王食子那个事件,姬昌受胁迫不得不吃掉自己长子的肉做的肉饼,非常沉痛地回到了故乡——那个画面让我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这个父亲当时内心经历什么样的强烈情感的冲击、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殷寿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用这么残酷的方式去摧毁他的政治对手?这个事件对姬昌姬发的家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我认为的最核心最强烈的事件,如果没有任何条件拍那些战争场面,这个家庭事件,这组人物是我一定要拍的,它是整个戏最核心的部分,不可以被删减,但是我们要把这件事重新梳理,让它真的符合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这些情感和动机。
还有一组人物关系是殷郊和他的父亲殷寿,殷郊很崇拜自己的父亲,妈妈被妲己杀死之后,他要复仇,结果被父亲推上了断头台,侥幸被仙人救走获得了法术,准备找父亲复仇,但最终还是回到父亲身边,成为父亲的捍卫者,阻挡从小一起长大的姬发。
殷郊作为儿子和他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我特别想探究这样矛盾的关系。这两组父子关系,两个家庭,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核心要素,如果要改编这个故事,一定要从这个出发,讲这两个家庭的故事。
父亲处死儿子这件事是很难发生的,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和非常明确的目的,才会做出这样极端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把殷寿的人物立起来:首先,他是一个野心家;第二,他害怕失去权力;第三,他要清除所有的异己。

他做的这些事情都有他作为一个政治野心家的非常具体的目的,而不是被妲己蛊惑了,我觉得那样就没力量了——作为一个反派,他挑战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和正常人的道德观念,他要有充足的理由我们才会相信,所以,首先要在剧作上让观众相信。
妲己,殷寿,姬发
《封神第一部》里的妲己也有很大的改动,我不喜欢《封神演义》里对女性的贬低,说她们是红颜祸水,所有邪恶的事都是女性策动的,这首先不符合我对女性的看法,不符合逻辑,不平等。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也是那些政治家推卸责任的方式,把罪责推卸给女性,是女性污名化的一种方式。
这些邪恶就是殷寿本人内心里有的,有邪念,妖孽才会依附,它们只是工具,所谓的妖精法术只是工具,因为你心里面有野心、有恶念,要去争夺权力。所以妲己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只是想满足殷寿目的。

殷寿的血帮她解开了封印,她无非就是想要回报他,“你有什么愿望?我帮你实现”。她不管这件事是正义或者邪恶,因为她是一个狐狸,目标就是生存。刚好妲己有一定的法力,可以帮助“恩人”实现愿望,在这种前提下,殷寿这个人物的野心是我们要探讨的目标。
无论是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其实都通过角色来演绎人性的复杂性和极致性,殷寿和姬发其实是极致的对比。
第一部里,殷寿和姬昌两个都是王者,为王之道完全不一样。后者是一个仁慈的父亲,一个充满爱心的、睿智的、有坚定信仰的人,后者则是为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欺骗整个天下苍生,包括欺骗神明。
所谓成为天下共主,并不是要去统治某个地域,而是要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你要有坚定的信念,要在所有的挑战和压力面前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这可能是神话史诗类型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接近于心理学层面的部分,所有的神话史诗其实都是心灵成长的故事。
姬发是有英雄观的,一开始是盲目或者天真的,但逐渐发现真相后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整个故事的剧情发展和戏剧冲突,其实在讨论这些基本的观念——我们应该坚守什么样的人性底线?结论是善良的力量最终让我们成为生命的王者。
人性的冲突,人性的选择和人性的成长,是观众到电影院所观看的重点,视觉奇观必须附着在前者之上,《封神第一部》才会被大家真的喜欢,否则只有那些炫技的部分,电影没法看,我也没法拍。

再谈工业化
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讨论电影工业化的问题,我自己总结的是三个层面。
首先是创作层面,一定是类型化创作的,任何电影都有类型范式和标准,文艺片也是类型之一,有自己范式。要是一个娱乐倾向的(电影),比如动作片或冒险、奇幻电影,也要达到这个类型的创作基本水准和制作标准。
第二个层面是制片管理层面,尤其是幻想类型这种本身技术复杂的电影,要有科学的工作流程和方法,这个是我们探讨得比较多的。《封神三部曲》剧组的分工非常细致,工作流程非常清晰,部门配合非常的默契,所以大家看到的是工作现场非常有序,效率非常高。

制作流程管理方面的工业化问题,需要充分的前期准备。我们前期建组筹备整整两年,拍摄是一年半,漫长的工作周期,庞大的剧组分工,整个三部曲先后在剧组注册的工作人员又8000多人,有438个拍摄日。
《寻龙诀》是我之前拍时间最长的,也只有141个拍摄日。但是《封神三部曲》单组拍了342个拍摄日,这个工作量和制作的复杂程度下,怎么去管理这个团队,其实就需要工业化的和方法。

第三个层面是关于科技应用方面,很多人谈到工业化谈的是科技应用,什么虚拟拍摄、动态捕捉和电脑视效之类,其实是工业化技术方面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些东西一直在更新,就只是制作环节的一个规划问题。对像《封神三部曲》这样的项目,是有一个视效技术的大的升级的。
视效技术分两个很重要的层级,电影视效有最重要的分水岭,就是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无生命体,比如说是数字场景、数字建筑,粒子的崩解,灾难片里的那些,但更难的是有生命体的视效,在整个电影视效的层级里,最高难度叫有生命体的视效。
比如《封神第一部》里的数字角色雷震子,还有九尾狐、墨麒麟、龙须虎等数字生物生命体,还有大量的集群动画数字人,就你们看到所有那些战争场面里全部都是数字人,这种有生命体的视效是最难的,但整个《封神三部曲》里充满了这样的镜头。
《封神第一部》雷震子

《封神第一部》可能就有1700个视效镜头,第二部第三部里会更多,当时国内不能完全完成这些,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自己成立一家公司,来平衡创作的各个环节。比如说在中国选择所有的概念艺术家,因为中国人的故事,审美必须要中国人来参与,而视效艺术家,要从全世界寻找。整个视效的制片人要全球去组织团队,有的最核心的部分是我们自己来做,比如雷震子、墨麒麟这种最难的数字角色和数字生物,都是我们做的。

有些分解层级的,都分在全世界不同的视效公司,最终我们来做全流程的管理,组织高难度的创作,再分包8个公司一起来完成整个的电脑视效的所有制作内容。当时正好是在疫情中,远程协调完成这么大体量的视效工作难度其实很大。
现在回头想,很多事我都没有第二个选择。因为我本身做导演的工作,每天都面对好多的选择判断和决定,我的工作就是回答别人的问题。“导演,这个行还是那个行?导演,这么写还是那么写?导演,这么演还是那么演?”就永远都在做判断和决定,难免会怀疑,我的决定是对还是错?
但每一次的选择,最后都回到我做这个电影是对的。这个选择让我非常踏实,因为我有好多问题要去探索,有好多知识要去学习,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它有难度,所以能激发人特别强大的潜力,这种有挑战性的项目对创作者来说是有刺激的。
在拍电影之前,我做了十年的当代艺术,但我还是希望做从精英艺术转向大众和通俗的艺术,选择做一个主流的娱乐电影导演。艺术本身和表达的方式没有高低之分,仅仅在于作品的质量和最终呈现出来的精神品质,通俗不意味着肤浅。

创作者必须要用通俗的方式去表达观点,探讨的主题有一定的公共性,比如说神话史诗,它必须通过电影院传播给观众,不能走小众的方向,不能走精英化的方式,因为神话史诗就是公共的。它是探讨我们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会选择这种类型,继续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