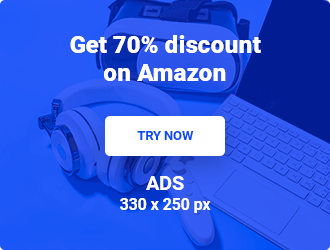从影评人转型导演,她用伪剧情片刮骨疗伤



美犹似置身黑暗里
苏七七导演电影长片首作
《长谈》访谈
访谈采写:许金晶(影评人,《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和《一个家族的电影史》(即出)编著者)
2023年7月1日下午腾讯会议视频连线访谈
访谈整理者:张珈源
之于独立电影艺术电影影迷来说,“苏七七”是一个极度熟悉的名字。之于影评人,她出版过多部影评专著,持续影评写作二十多年,以诗意、锐利而兼具温情的笔法著称;之于电影学者,她拥有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学位,并在浙江师范大学从事电影学教育,真正做到了“以电影为志业”;之于电影策展人,她担任过海内外多个重要电影节展的评委、选片人,并策划过“杭州平行影像周”等多个艺术电影的系列放映活动。而如今,苏七七跟电影深度结缘的身份角色上,又要加上“电影导演”这一项内容。她编剧、导演的长片首作《长谈》,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举行了全球首映。
为什么在影评人、策展人、电影学者等跟电影相关的多重身份之外,仍然要试水电影导演这样的全新身份?这部《长谈》的创作动机、影像气质与意义指向何在?这样一部作品,跟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刚刚过去的“巨变三年”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围绕新片《长谈》,跟苏七七导演展开了对谈。

苏七七
Q&A
许金晶:您早已兼具影评人、策展人、电影学者等跟电影相关的多重身份,为什么还会在观察、研究跟策展之外,想尝试电影创作的角色?《长谈》这部电影,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创作冲动、并最终孕育和诞生的?
苏七七: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对自己拍电影是没有想法的。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主要写评论和随笔,职业身份是写评论,也会在豆瓣上写写随笔。以文字作为表达的工具,对我来说是更训练有素的,某种意义上也更有安全感。很多创作者可能因为热爱电影而去拍电影,拍电影是他们很喜欢、很向往的,所以找主题、找方法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电影是艺术形式的一种,文学呀,美术呀,同样能够给我带来审美上的共鸣和愉悦。我拍电影不是因为我很喜欢拍电影,而是因为当我有某种表达的必要,我感觉到我非得表达一个什么东西不可时——我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我用什么形式来表达是更好的呢?用评论来表达就足够了吗?用随笔来表达就足够了吗?我发现这可能是不够的。然后我想也许可以拍一个电影。这个选择里包含着我对我自己能力和性格的了解和判断。电影可以有一个团队,聚集更多人的想法和力量,并且在搭出一个团队之后,能互相支撑,把电影给做出来。电影这个形式对于我要表达的内容、我这个阶段的状态等,都应该是比较好的形式。
2021年夏天我的状态很糟糕,处于严重的自我怀疑之中,但同时又有一种“真的只是个人的问题吗?还是这个世界的问题更大?”我觉得自己好像被逼到角落里了,但这种被逼到角落里的状态激发了我的一种反抗——我都被逼到角落里了,还能做什么呢?我想只有创作能让我从之前的状态中出来,对创作还抱有某种意义上的信念和信心。做一个作品,就是我能够找到的,抵抗和反击把我逼到角落的这一切事情的方式。我得靠创作从低谷中出来。只要我还在创作,那这一切就打不倒我。

接下来就是,电影到底要拍什么内容,怎么拍?这需要很具体的计划。在有了拍电影的想法之后,我觉得,既然这是我自己的问题,那么我就只拍我自己的生活。要拍一个纯虚构的电影,对我来说也是很困难的。我要拍的是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影片,但是具体拍哪些东西一开始还比较模糊。可能在9月初的时候,我跟阿波说我想要拍个电影,阿波很支持,我跟他说我们要自己来演的时候,他同意了,但是我还是犹豫彷徨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和结构应该是怎样的。当时先浮现出来的想法是我可以拍一对中年夫妇的一个周末,这是一开始就比较清晰的内容方向,我觉得这是比较可行的。我是第一次做电影,首先会考虑,怎样的东西是我能操作得动的,就好像要搬一块石头,你会知道哪块石头是搬不动的,某块石头是搬得动的。我觉得如果把问题集中到一对中年夫妇的一个周末,把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记录和剧情相融合,这种方法可能是可行的。
有了这个方向之后,电影还缺一个开头,不知道这个故事从哪里讲起。一开始只想到是周末,但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如果直接从早餐那场戏开始会很怪,于是就搁置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们各自忙各自的,看看手机什么的,阿波突然跟我说,我们一起来读会诗吧。读完诗之后,我们就去睡觉了。这跟片子的开头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睡不着,积郁于心,难以言语,我起床离开卧室,一个人走到楼下。呆在楼下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这就是我的电影的开头。我想讲的是两个人,他们在身体、生活、精神上的亲密度都如此之高,但是内心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是自己要独自承担和面对的,要向对方说明自己处在怎样艰难的状况中,是很困难的。我马上找张纸记下了这个开头。有了一个夜晚作为开端之后,好像问题有了一个切口,可以把它给展开了。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周末要通过什么方式来展开你的问题?用遇到什么人,聊什么天承接?“万事开头难”,有了开头之后,我非常顺利就写出了整个框架。从这个夜晚到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对话、我们各自忙的事情,到中午的时候音洁和韬哥来访之后的两场吵架,他们两个人吵架和我们两个的吵架,然后去咖啡厅,傍晚的散步,遇到一场戏剧,晚上的时候我们重新找回了那个亲密的点,以及第二天我们去东明寺,这个大框架就都建立起来了。只有两场戏在一开始的框架里是没有的,一个是萧耳来找我们,那场戏是我最后补上去的,感觉这里需要一个过渡段落,还有一个就是下雨的那场戏,也是后面想出来的。就这两场戏是后面补上的,别的都是直接在框架里一下子浮现出来的,很快就把它写出来了。其实框架也很简单,我不需要非常完备的剧本,一张A4纸就足够了,完成了最重要的剧本阶段的准备。
许金晶:这部影片有着类似传统戏剧“三一律”的严整结构,即故事都是在一个周末里发生的。周末是暂时摆脱了本职工作中身份角色的时间,可以视作本职工作此岸之外的彼岸,但彼岸又是跟家庭成员深度接触的主要时间。片中一以贯之出现的,就是你跟本职工作,或者说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之间的一种紧张感与张力,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脱离出你跟家人、跟家庭成员相处的逻辑、关系和命脉的,影片最后还是以一种和解的方式凸显出来。所以我觉得你虽然只是从自己的可操作性角度考虑,选择了周末这个时间,但是周末自然延伸出的一些矛盾与张力,其实跟主题是天然契合的。故事的主体始终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妇、而且是你们夫妇本色演绎,这样的时空与人物设计,基于怎样的考虑?
苏七七:是的。紧张感是这个电影的出发点。这种紧张感来自于我的工作,一个知识分子和身处的体制之间的紧张感,以及与时代的状况之间的紧张感。

许金晶:包括你们夫妇在内,片中出现的所有相关人物,都是以本名本色出演,甚至影片的故事推进,也呈现出一种自然化、日常化、随机化的类纪录片风格。在这部电影的文体设计上,你有着怎样的考量?
苏七七:我设计的文体就是所谓的“记录为里,剧情为表”。它是个剧情片,但我认为它本质上是个纪录片,甚至你可以把所有的场景都理解为现实生活的某种搬演。现在有个概念叫“伪纪录片”,这几年还挺多的。我觉得《长谈》可以界定为“伪剧情片”。当然文体上如何评估它是一个纪录片还是一个剧情片,大家还是会从行业约定俗成的规则来看,包括外在的形态以及操作的方法。所以还是得把它当做剧情片去讨论,去参展,而不是把它归类到纪录片里去。我其实无所谓文体,因为不管剧情片还是纪录片,它归根到底在于你能不能讲出某种“真”的东西:是不是有非常真的问题,是不是有非常真的困境,以及你是不是表达出了那么一点点真的可以托住这些东西的力量?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没有那么重要,只要它内在有某种真的东西就可以了。这是文体上的考量。
另外就是文本方面的考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结构。我在影片中间留出了很大的纪录片式的即兴的可能性,但它还是需要一个相当严谨的结构。虽然我只有一张A4纸,但这张纸上是不是有一个严谨的结构,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整个结构有点像论文,比如说最开始的那场戏就有点像绪论,而接下来早餐的那场戏,把电影后面会发生什么都说了。比如我说下午音洁要来,明天我们要去东明寺,诸如此类的,它像一个目录,像一个提纲。这场戏就已经把提纲送给大家了。接下来每一个部分的内容都有它相对应的要讨论的要点,比如说音洁的那场戏,我们要讨论的是女性知识分子的处境,一个是工作的压力,另外一个是作为母亲,在家庭生活中要承担母职所带来的压力,有时这个压力是非常令人崩溃的。
音洁夫妇吵架的那场戏完了以后,我跟阿波的吵架其实是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我们要再推一波,把它推得更高一点,更深一点。争吵完了以后阿波去找我,设置在咖啡馆,那家咖啡馆其实就在我们小区外面,我跟那个老板也确确实实是经常聊天的好朋友。这个部分,我想引进一个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视角,就是说普通的女性,咖啡馆的老板娘或者沫沫同学的妈妈这种比较松弛的状态,有时候会给我安慰。生活对她们来说好像比较放松一点,因为她们不在生活之外再追求、再思考一个更观念性的东西。我想要用生活化的东西来对冲一下前面呈现的非常紧张的情绪。

这段结束后,我的剧本里面是阿波来找我,我们去小区的长椅上对话。这段对话非常重要,从工作和家庭的问题进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就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怎么回事。开始时问题还是我的,但到后面阿波的主动权加大了,他把这个片子往形而上的层面再推了一下。我前面给到的是具体的、现实中的问题,而他从诗歌的角度去观察与呈现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以及逃脱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它并不明确,但往空阔的方向上去走了走。我也很需要这个主题的开拓,如果只是谈到我的问题为止,没有往哲学的方面推一推的话,我总觉得这个片子还有点难以立住,还不够,就只是一直沉溺于自己的困境中。这时候言语就失效了,不像前面的内容,可以谈得很清楚,而只能在戏剧、诗歌、音乐的混合中给到某种想象的空间,没办法清晰地把它说出来。阿波的困境是一个诗人的困境,诗人与世界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他讲到这个世界走向了破碎与虚无,但他试图在偶然性中抓住某种必然性,抓住永远在一起的可能性。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片子的落脚点,面对所有的困境、所有的想象的时候,最终还是得落实到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可以完成情感上的共情,可以达成精神和肉体的亲密和融合,只有这才能够真正地托住我们,帮助我们面对和承受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困境。
许金晶:这部电影里,作为女主角的你的精神困境,跟包括疫情在内的大的外部环境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你的精神困境的核心矛盾何在?而这种困境的疏解(虽然可能是暂时性的),是如何通过影片的有机叙事去呈现的?
苏七七:我的困境一方面来自工作,另一方面,女性的困境还在于家庭。作为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就是整个世界好像从自由主义走向了保守主义。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成长在自由主义的氛围中。我们在自由主义的氛围下度过了我们的青春期、成长期,但到中年的时候,又发现一切好像钟摆一样站到了保守主义这一边,其实内心是挣扎的。我们经历过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但是疫情好像直接终止了全球化的幻景。当然全球化其实不是被疫情终结的,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只是当疫情来到来的时候,它终结得这么突然。突然间飞机不能够再飞来飞去,到处都是路障,处处都要出示证明,种种的封闭,种种的阻隔,这样的状态,肯定是令人抑郁的。阿波说我们好像到了一个分裂的、破碎的时代。在这个分裂和破碎的时代,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是困境所在。

许金晶:之于空间表达的敏感,成为本片的重要特色之一,在空间的选择与调度上,经常让我想起张律导演的电影。影片的第一空间是“家”这样的私空间,在相关空间的布置、设计、调度与把控上,能不能谈谈你的具体安排?
苏七七:空间的设计其实就是从室内空间到室外空间的过程。一开始是在家里,第一个镜头是从卧室开始的,像是洞穴一样,然后过渡到家里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客厅。之后我们争吵到了街上,再到河边去散步,但还在城市里。最后的寺庙就不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自然环境中。从室内到室外,是从很封闭的洞穴一样的抑郁的状态,一直向外突破的过程。
许金晶:家里这段拍摄的内容,包括布景也是没有刻意地调度,是自然为之的?
苏七七:因为就是在我家拍的嘛,布景肯定是没有的。我这个片子是没有美术的,基本上没有刻意的设计,拍到了卧室,拍到了客厅、阳台,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动,摄影师会追求画面更好看一点,出于构图的考量,就稍微调整一下,整洁度可能比我们真实生活稍高一点。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它本质上是个纪录片的原因,它完完全全是在一个真实的空间中。所谓真实的空间指它的功能、它的历史、它的状态都是真实的,每一个空间都是真正的空间。我从家里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能给我安全感。我可以非常自由地调度这个空间,我爱怎么用它,就怎么用它,能很自由地思考怎么用它。就比如墙上的那幅字“始制文字,乃服衣裳”。这是《千字文》里面的一句话,讲文字刚刚开始,人有了衣服,步入了文明状态。这就是读书的问题嘛,有文字,有衣裳,在文明的末梢才会有这样的困境。
许金晶:在没有任何调度的情况下,这些背景道具它自然地与影片意义产生关联,其实它跟片子的主题是正好对接起来的,是天衣无缝的。
苏七七:那幅字也不是我临时挂上去,现在它也还在那个位置上,是沫沫小的时候刚刚开始学写毛笔字的时候写的,他学隶书《千字文》的时候临了一张,我觉得蛮好,就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从那个时候起,这幅字已经在我家挂了十来年了。如果能与主题产生某种对照关系的话,它是一种天然的对照关系。
许金晶:而跟“家”这样的私空间相对应的,是小区、小餐馆、咖啡馆、剧场这样的公共空间。在疫情仍未消散的故事背景下,这些公共空间对于你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每一个空间里的对话与故事,又是怎样调度和设计的?

苏七七:我们就是在管控的间隙拍的。咖啡馆、餐厅就在我家旁边的街道上,都是我的街坊邻居,我在这个社区住了十几年了。这是我头一次拍电影,但是我得到了特别多的支持,这些支持不完全来自于志同道合的做电影的小伙伴。小伙伴的支持,我倒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大家肯定会支持我。但是有趣的是,咖啡馆的老板娘和朋友、餐厅的老板、寺庙的和尚朋友,大家都超级支持我。
比如说咖啡馆的那场戏,其中的两个朋友都是所谓的“妈妈团”,因为附近有个小学,我们都是同一个小学的孩子的妈妈,平时也都很熟悉。我跟她们说,我要在咖啡馆拍一场戏,让她们来演一场戏,她们就很开心地过来,都没有问我要拍什么就说好,所有的人彼此之间都有非常大的信任感。
许金晶:那就是说也不需要背台词,你告诉她们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摄像机在旁边,自然而然地拍摄出来的这样一个状态。
苏七七:我跟她们说要在这里拍一场戏,这场戏是我的状态有点低落,你们先在这里玩塔罗牌、聊天,聊聊你们最近什么样,然后把对话最后过渡到我的状态,安慰我一下就ok了。那聊什么天呢?比如说佳佳讲了一个小柠檬的故事,其实另外两个人也有小故事的,几个女人在咖啡馆的吧台上聊天的时候都会讲一些小事情,所有的台词、所有的事情都是她们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编给她们的。佳佳的故事是自己想的,芳芳和刘韫的故事也是她们自己想的,只是觉得有一个故事就够了,那两个故事后来没用上。这都是拍这场戏之前的一周和她们聊出来的,跟她们聊完了以后,我就整理出一个两三页纸的台本,拿着这个台本,我们约个时间对对戏,对完了以后就可以开始拍。因为所有的台词和事情都是属于她们自己的,所以不存在背台词的问题。
这个片子里的每一场对话都是用类似的方式演绎或者创造出来的。比如音洁那场很大的戏,台词也是我们商量出来的。音洁是一个表演能力非常强的人,是个非常好的演员,她是教戏剧的老师,教理论也教表演,她的表演对这部电影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音洁在现场的时候不需要我做任何的指导,她会随着状态的推进,自己找到一个更高的点。
因为剧组成员都有工作,我们不是所有的戏连着十几天拍完的,而是一周一周拍,每周末拍两三天。所有的台词不是编剧给到演员的台词,都是演员自己生成的。
许金晶:你们夫妇跟音洁、韬哥夫妇之间的四人餐桌对话,是这部电影里最具戏剧张力、爆发力,也是最为精彩的桥段。比如阿波在这个过程中看似闲笔,闲庭信步地给大家分菜、布菜,这在整个四角的冲突戏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出戏,你是怎么设计和安排的?在这出戏的镜头语言聚焦与整体设计上,你有哪些自己的考量与交待?能否具体谈一谈?
苏七七:演员真的非常好,你说闲笔,但这些并不是阿波完完全全自发的反应,而是有考虑的。他考虑到这个镜头里如果没有任何动作会很呆板,所以他要去给大家夹菜,动一下汤勺,只有他一个人在默默地维护着镜头的动感。不是我的设计,我的演员们都很有主动性。

许金晶:从动态的角度来说,电影是一个图像,是动态化的艺术。我觉得影片每一帧的构图拿出来,也是非常精彩,对比感非常强烈的。
苏七七:阿波的镜头感远远比我好。他在镜头中间的时候,会非常自觉地思考:我站这个镜头里,我要做些什么。但一般人是不会这么想的。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经过任何表演训练的人,我就不会这么想,如果有动作也是我自己的动作,而不是说我在镜头中,所以我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他比我更有表演的天赋。
许金晶:所以你的长片首作能呈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成型、成熟的状态,其实与从演员到整个团队选对了人也很有关系。
苏七七:这是肯定的,演员们的水平都很高。
许金晶:其实片子里的这些主角,周末都是经常参加公共沙龙的,用戈夫曼的理论来说,我们都是在一个舞台上演戏的人。
苏七七:是这样的,包括萧耳呀,音洁呀,杨岚呀,都是这样的,本身就具有某种剧场性。
许金晶:电影的片名叫作“长谈”,为什么会强调谈话、或者说对话的重要性?影片里你们夫妇之间展开的种种对话,文本设计和即兴发挥的成分各自有多大?这种谈话或对话,在公共生活受阻的背景下意味着什么?有没有更大层面上的象征与隐喻?
苏七七:这部电影要讲的是困境,这个困境实际上不一定能得到解决,但是我会觉得我们得找到一个东西把它给托住,这是我的思路。我们能以怎样的形式呈现这个困境?一个叙事电影应该通过展现某种状态,自然而然地把某种困境给呈现出来,而不是直接地把困境用台词给说出来。这是通常的做法。比如贾樟柯拍《小武》,他就是完全通过事件、场景、情节、细节,去呈现出来。但《长谈》要呈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困境,势必要以谈话作为一个重要的渠道。我所喜欢的导演,比如说侯麦或者伯格曼,他们的电影里,台词占据着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一些东西是你必须去说出来的。对于我来说,这是我一开始就明白的:我们的电影肯定是一个把问题说出来的电影。
电影的语言是视听语言,通常而言,在一个叙事电影里,主要信息是由视觉部分给出的,我这个电影可能倒过来,它的核心信息是通过听觉部分给出的,视觉只是给到这个信息的场景,比方说我们聊天的内容,换一个场景是给不到的,视觉是为听觉信息提供某种场景的支持。这是我一开始就这么想好的,必须这样做及只能这么做,这是由我要讨论的困境的类型决定的。

许金晶:琴人杨岚,是你在熟悉的好友之外,安排的一位重要配角。杨岚跟女性朋友在小餐馆的那场对话,你是怎样去设计的?他俩的对话,跟你们夫妇与萧耳之间的对话,是不是能构成某种互文与互动关系?杨岚这个人物,以及他的古琴音乐和古琴生活,在这部电影的叙事和表达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苏七七:我们其实是认识非常多年的朋友了。他刚刚来杭州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他是阿波的古琴老师。这场戏就是刚刚说的后面补的。在长椅上的对话结束之后,如果我们接下来直接就去河边散步,即使从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对,而且太单调、单薄了。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这场戏,但后来觉得这个地方不行,得再补一场戏进去。那我们就在这个晚饭的时间段,安排朋友来一起演一下,丰富一下内容。然后就列了几个可能参与我们晚饭的朋友,萧耳和杨岚都是我们的考虑的对象。
我们这代人,刚刚说的,在自由主义的氛围中度过了青春期和成长期的这一代,要回顾一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童年与成长,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一步的。呈现中产中年知识分子的状态最好能有一个东西能触及到过往,这个状态才能显得更实一点。如果晚餐这段需要起到这种叙事作用的话,萧耳就是最好的人选。萧耳和阿波是大学同学,他们的成长环境又很相似,都是在杭州边上的水乡小镇长大的,也都是从小地方到城市中的上一代“小镇做题家”,随着时代的红利,很顺利地在城市里安家,也有自己生活和精神的追求。所以这部分萧耳来讲的是最好的,萧耳是个很好的小说家,她给我们的这段台词也是很完美的,讲她去看父亲,就讲到小镇的变化。
但当时我们觉得好像还是太单薄了,有一种意图过于明显的感觉,还是需要另外的东西来发散一下,不要这么呆板。我想,可以让杨岚和顾泠他们两个来谈话。顾泠就在我们对面的小区住,我们俩跟杨岚和顾泠是真的在那个小餐馆偶遇过。至于他们两个在那里要谈什么?阿波很喜欢古琴,他跟杨岚学过一段时间古琴,古琴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很难说,它更像是一种调性。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文化的洗礼,比如说我们思考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们的思想方式是很西化的,我们总是在读西方哲学家的书,读西方当代哲学比中国古代哲学更多,因为它对当代生活更有阐释力。但其实我们文化的调性与根底是来自于古琴,来自于山水画的。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清楚,因为比较匆忙,这段戏又是临时加的。所以找他询问意见,问他和顾泠要聊什么比较好,他和朋友在小餐馆也会聊旅行的时候遇到的事情,他就写了一小段话,我觉得也挺好的。这段戏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我们特意做了场景的设计,我们在杨岚的旁边还放了一个古琴,包在琴囊里。
我跟阿波在河边散步之后,有一个河边的空镜,就用了一段成公亮的古琴曲《沉思的旋律》,杨岚弹的,那段音乐和这段场景可以形成一个对照的关系。我跟阿波在河边的谈话,从一开始比较沮丧、低落的状态,又过渡到和好,然后一起回想起过去共同走过的时光,并且觉得偶然性中我们还是依然可以有所握持的。这不完全是哲学观念的逻辑推理,而是我们共同受到了古典文化的熏染,在这样的文脉中间形成自我。所以我们才会在认识到必然性是不存在的那一刻依然可以希望有事物能够延续下来。其实我们也是跟着直觉在走,跟随着某种“好像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直觉,就应该找他,因为我们之前就遇到过他,他想讲什么,就让他讲他自己想讲的东西好了,最后又觉得这些都能贯通起来,挺有意思的。
许金晶:这部电影肯定会是影评人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我相信电影未来问世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影评,我到时候肯定要到豆瓣上再去浏览一下。
苏七七:我自己觉得写评论是隔岸观火,即使有着再强的共情能力也还是隔岸观火,而创作是以身试法,自己去试。很多情况下是跟着直觉和偶然性在走,想的没有那么地清楚。
许金晶:聚餐的那场戏,包括聚餐之后,你们夫妇对话的那场戏,里面核心的戏剧张力或者说矛盾冲突,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你那一句台词,“学术体制是对知识分子的规训,其实应试教育体系也是对小孩子的规训,我们自己不想被规训,然后呢,又加入了规训小孩的阵营”。我对这一段话印象特别深。
苏七七:一个是制度的问题,一个是家庭的问题,二者重叠在一起。我们自己想抵抗制度对自我的规训,但是又好像不能不去规训孩子,因为感觉到如果完全不规训的话,你又有一种恐慌,有一种孩子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恐慌。
这个片子其实是在沫沫高一的时候拍的,说实在话,这个片子对我和沫沫的亲子关系是有着非常良性的作用的。他住校,每个周末回来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规训他,因为他一回来就是片场,家里至少有10个人,他要跟我聊点什么,要等到很晚空下来的时候,才能跟我聊一小会儿,讲他学校的事情或者他自己的事。
在写出了台词以及做这个片子之后,我确确实实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孩子来说,自由远远比规训更重要。而且自由能给孩子的创造力、想象力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力。到高中以后,他其实是非常“不务正业”的。与普通的高中生相比,他用在应试教育上的时间非常少,大部分业余时间可能在搞音乐。我曾经去规训他,叫他好好学的东西,他学得也还可以,但是他自己自发去搞的东西,才能达到更高的高度,是我想象不到的高度。所以还是要给到孩子很大的自由和选择,让他自己去释放青春期的创造力,这是珍贵的生命的原动力。这个片子里面有阿波的诗,也有沫沫的音乐。家人在一起,这个家庭空间并不是你规训我,我规训你的地方,比如说阿波以一个妻子来规训我,我以一个儿子来规训沫沫,而是每个人都在创作:阿波写诗,沫沫在做音乐,我在拍电影,那么这个家庭空间其实是可以非常有创造力的,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的,三个人都是创作者,互相之间就像一个创作者的共同体。家长可不可以从规训孩子的状态中跳脱出来呢?我现在觉得,如果能真的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可以跳脱出来的。
许金晶:根据卡夫卡小说《判决》改编的戏剧,成功将影片的叙事与氛围营造推向高潮。能否介绍一下这部戏剧的相关背景、以及在影片叙事中扮演的角色?
苏七七:《判决》戏剧的导演,就是片子最后坐在那里聊天的两个年轻人之一,那个长头发的男生,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青年导演。《判决》这场戏很重要。这个时候电影在从实到虚,如果光靠诗歌的文本,诗歌是没有视觉的,要有东西依托一下才能够从实到虚,戏剧是我能想到的从实到虚的最好方式。如果影片后半部分在现实层面上无法推进了,我就需要一个戏剧来推上去。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走到大屋顶旁边的时候,看到一部戏剧,然后就可以从戏剧进入诗歌,进入到一个比较形而上的层面。关于戏剧,我是希望朝然真的把电影里的这个戏剧《判决》作为一个独立的戏剧给排出来,然后他真的排出来了,我这个电影做好之前,他的戏剧都已经在大屋顶公演了。我的剧组很小,常常一人多用,朝然既是戏剧的导演,也是演员,还做了很多的设计类工作。
许金晶:这部电影多少具有一种“私影像”式的家庭电影色彩,甚至配乐、文学文本等,也都是分别由你儿子和丈夫完成。沫沫(儿子)的音乐和阿波(丈夫)的诗歌,在影片中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跟你的影像叙事之间,能够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苏七七:诗歌是很重要的。在对问题的讨论中,有时达到某个点后,就很难只在逻辑的层面上推演。有什么东西能超越逻辑呢?这个时候就是诗歌。诗歌放弃了逻辑,走向了某种能够直接带来超越性的语言。我觉得这个位置上要有诗歌,但诗歌怎么进入电影?我们现在的设计就是先有一个戏剧,然后阿波进入戏剧之后把诗歌带出来,现在觉得还是很有效的。
我们是一个创作气氛很浓郁的家庭,互相给看看自己写的做的东西,也互相讨论评价,沫沫的音乐其实不是为这个电影作的,但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找到了比较贴合的东西,等电影做好了以后,他又为电影去改了一下,做得更贴一点。
总体而言,在这个时代,大人小孩都在各自的困境中,不管是我们片子里面讲到的这两个小孩,还是大人。然后阿波去写诗,或者我做电影,或者陌陌做音乐,某种意义上,都是非常自发地从自己的天赋出发,去找一个突围的方式。
家庭是一个气场,我们感受到的东西是非常一致的。虽然艺术形式不一样,但我们其实是互相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用沫沫的音乐来配阿波的诗的时候,感觉非常吻合。他的音乐是在这个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本质上是同类的。

许金晶:影片的转场并不多,但每次转场时的空镜头和相关布景设计,都让人印象深刻。能否介绍一下这些空镜头的具体设计安排和用意?
苏七七:空镜很重要,我们后期还补了一部分空镜。我们的剪辑秦亚楠和胡力维是非常好的剪辑师,这个片子如果没有她们的话,我觉得都立不起来,特别是在后腰的那个部分。我们看戏剧,然后进入幻觉、诗歌,之后剪接到我们俩的特写,推进得非常好。之前我自己把素材连起来的时候是非常担心的,感觉很困难,好像推不上去,但亚楠剪了以后就完全立住了,剪辑是非常重要的,是真正的二度创作。我所有的合作伙伴都是朋友,包括亚楠,我们认识了很多年,互相之间非常了解。如果要很临时性地找一个合作者,说明与沟通想法其实是很困难的。我这个片子是个很小的项目,拿去找她剪的时候,完全是因为我们是很多年的、彼此非常信赖的朋友,她才接下来,是她对我的支持。剪辑的时候,她让我们在家里再补拍一些空镜,我跟阿波就用我们手机的4k模式,在家里补拍了一部分空镜给亚楠用,包括篇头的两三个空镜都是我们后来用手机补拍的。亚楠的剪辑有呼吸感,你那口气能透出来。一个剪辑师好就好在,她推的时候,能推得上去,透气的时候,能透得出来。
我们拍的家庭内部,空镜是很重要的。回到刚才关于“真”的问题上,空镜不是布景,本身就有着时间的累积和气氛的加成。赵晋,也就是我们的制片人,说要拍出那种在室内巡礼的感觉,甚至还给了我们一些参考片目。如何运用空间和空镜,在我们共同讨论创作的时候的一个重要议题。
许金晶:影片中,你们夫妇之间从冲突、和解到继续相守,这样的转折,其内在的精神动力与心灵密码何在?能否结合你们具体的日常家庭生活,做一些分享?
苏七七:我拍这个电影要讲的是困境,但我也非常明确,困境其实是解决不了的,就像伯格曼的电影,一个片子提出了一个困境,但也只是阶段性地解决,在某个点上能够找到一个着落点,没有办法彻底解决。我跟阿波之间的关系,其实还蛮超越婚姻制度的,既在生活上互相依赖,也在精神层面上有很深的互相交流,拍电影的时候以及拍完之后,我们的关系确实更好了。因为电影要把你所有的问题拿出来讨论,要一直一直挖,挖到最深的地方,然后讲最深的地方你该怎么办,有点像是刮骨疗伤。你有一个痛苦的地方,可能大部分情况是不去挖这个伤疤,但它会留在那里,甚至会溃烂,会死亡。但如果去挖了,在讨论的时候,你会很认真、很彻底地去看问题在哪里,以及在什么层面上我们可以去找到应对的办法。
所以,拍电影之后,我们有点像战友一样,“与子同袍”,这种关系甚至比夫妻关系更加坚实。
许金晶:我很期待这部影片正式公布之后的传播,因为尽管它聚焦的是一种私影像化的、个体化的困境,但是这种个体化是说每一个身处当下的个体所面临的共同的大环境,不管是疫情也好,还是整个外部环境也好,都是共通的。所以尽管影片非常个体化,但它其实非常具备公共化的共情效应。具体来说,比如影片最后的长镜头设计就颇有象征意义,能否介绍一下这个长镜头的具体设计安排和用意?
苏七七:拍电影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像影评人一样去拍电影,很多时候就是直觉,不需要论证,不需要逻辑。结尾下山的这个长镜头,我内心早就很笃定了。我们最后是去东明寺的,那肯定要从山上下来,不可能老待在东明寺,对吧?你走到了东明寺,有过那么一瞬间的彻悟。凡人的彻悟都是有时限的,就彻悟那么一分钟,最多了,然后又得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来,所以得从山上下去,这是必然的。那么为什么这个镜头对我来说是很肯定的呢?因为东明寺其实就是我们精神的休憩之地,我们去东明寺不是去一个寺庙,而是去寺庙里看我们的朋友,喝茶啊,聊天啊。因为经常去,很好地感受过这个空间,就知道哪个地方的气场能够出很有感染力的东西。因为那条下山的路我们车开过很多次,感受和经验都已经在我心里存了很久,只是现在把它放到这个电影里来。
开门的镜头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叫他开门的,当时我们从山上开下来,开到那里,然后开门的大叔就以为我们要出去了,他就打开了。特别好笑的是,这真的是我们拍的第一条。我们一般会多拍两三条备用一下,当时阿波开车,摄影师峥安坐在副驾上拍,阿波说那这条拍完了,我们掉头再拍一条,他就掉了头又开上来。那个看门的大叔就很奇怪,很郁闷,你们怎么不走。第二遍又从山上开下来,那个大叔就不给我们开门了,所以我们用的是第一条。第一条的感觉是比较好、比较饱满的,有的时候来很多遍之后,感觉就不太抓得准了。我们看到也很震惊,说哇塞,这个开门简直神来之笔。
许金晶:哪些影视和文艺作品,为你这部电影提供了灵感来源与创作资源?能否具体一一介绍?
苏七七:人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伯格曼式的。我的根基在伯格曼。从电影的角度上说,伯格曼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会不自觉地按他的思路来。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另外谈话式的电影,比如说侯麦,以及后来的洪尚秀,他们用一种很轻盈的小剧组的方式来做电影,用场景交换中不停的谈话来推进叙事,这也是可继承的传统。我不是编织、虚构一个非常有动作性的故事,而是靠场景和对话来推进叙事的深度。
另外我喜欢的导演,比如张律,真的有一个向他学习的地方,就是兔子那个场景,那个地方比较搞笑,这绝对是我向张律学习的,莫名其妙地来了个有趣的东西。张律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我很喜欢他荡开一笔的这种有趣。还有个华语电影导演叫李珞,我也很喜欢。
滨口龙介和洪尚秀是这几年东亚艺术电影最重要的导演。他们用比较轻盈的方式来拍电影,是低成本艺术电影学习的对象。从制作层面,可以做到洪尚秀这个程度,或者更难一点,做到滨口这样可能也可以。但是拍不到是枝裕和的程度,是枝裕和的作品就是很严格的院线电影,不是我们这种成本能够做到的,我们拍的其实还是极低成本的作者电影。
许金晶:电影的学术训练和长期的影评写作,各自在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产生出怎样的影响?
苏七七:在我的感受里,评论和创作这两件事背道而驰,创作是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地方都不知道,充满幻想又充满忧虑。评论是在一个建好的地方,回头感受与推敲它的意义,价值,历史沿革什么的。两者用的是几乎是脑子的不同部分,当然都要用心。
拍电影的时候,根本不会有“我是一个影评人,我知道怎样才是好的,我要按好的标准去拍”的想法。
拍电影的时候,只有一种“拍得再糟糕我也得把它拍出来啊”的心情。
许金晶:之于电影创作方面,有没有后续的创作计划?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这个新角色之路继续下去吗?具体是怎样的安排?
苏七七:应该还是会再拍的,第二部作品的想法还在不停地更迭,有的时候有一个思路,但是又会推翻这个思路,还在一个设想和推敲的过程中。
拍过一次电影之后,我感到拍不是特别难的。你要组一个团队,找到摄影录音等等建立起一个剧组,这个事情做过一次之后,我觉得不是特别难,而且我们的团队特别好,是非常纯粹的共同创作。最难的地方反而在前面,在剧本,有没有如鲠在喉想要表达的东西,有没有推动力去形成一个叙事性文本。如果这个准备得到位了,可能就再拍起来。
-FIN-

编辑:小甘
何以存有最后的希望?
豆瓣:il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