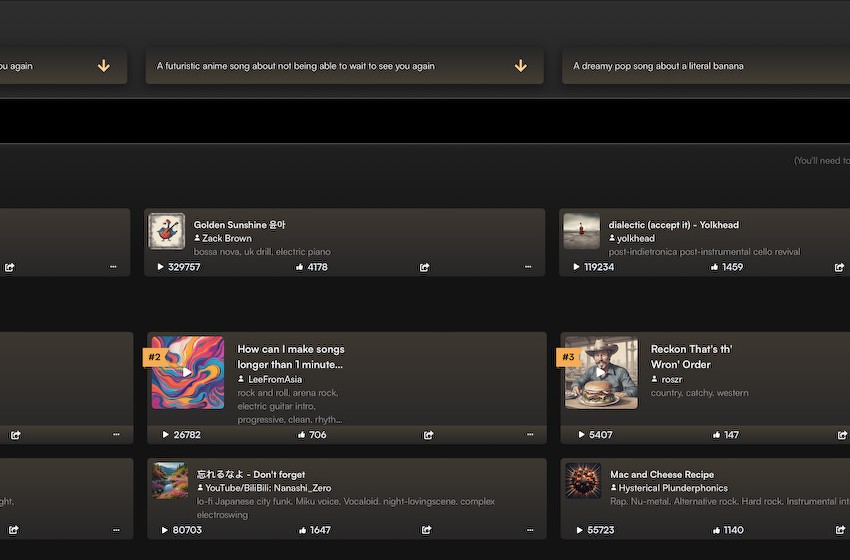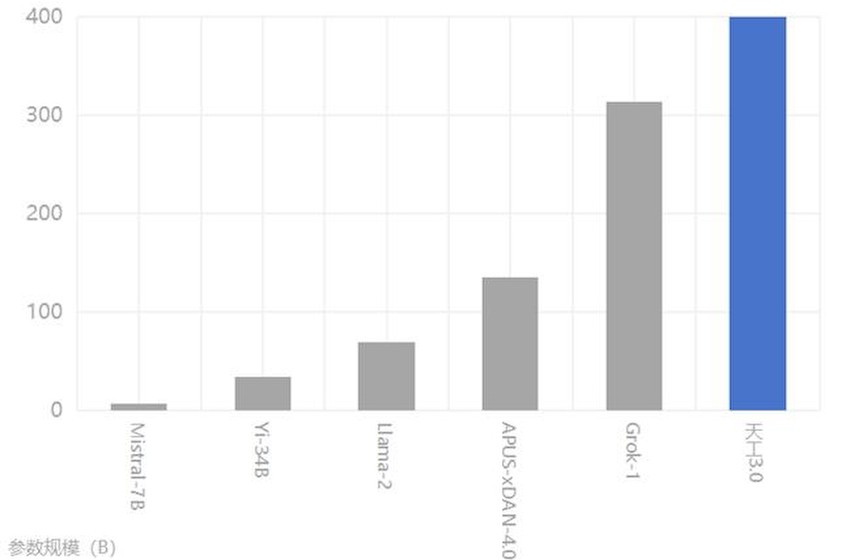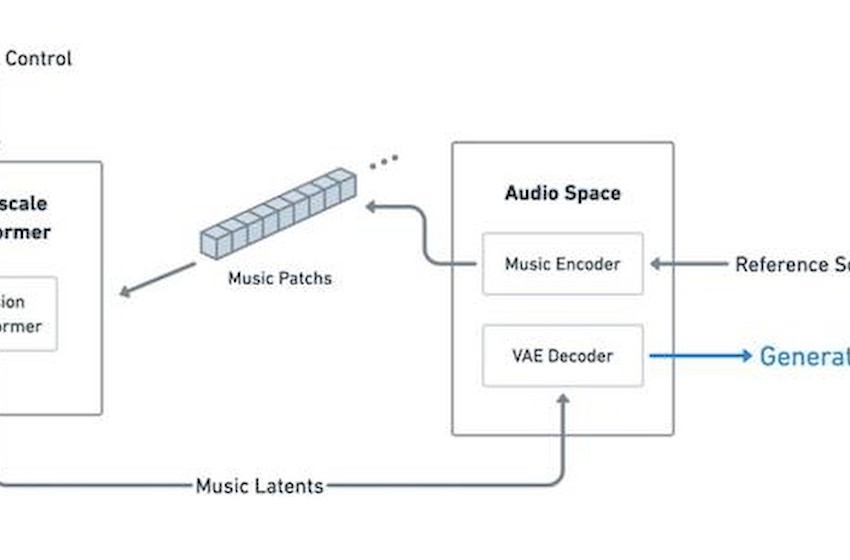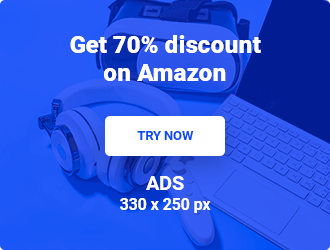ChatGPT时代,数据标注员还在搬砖
作者 | 袁斯来
编辑 | 苏建勋
肯尼亚内罗毕,一群年青人挤在逼仄的办公室,埋头在电脑上阅读一段段来自大洋彼岸OpenAI的英文字符。
他们工作的9小时中,要阅读、标注150-200段文字,每段文字在100-1000个单词之间。而这群人的薪水是每小时1.32-2美元。
当你和Bard和ChatGPT聊天时或许并不知道,它给出的每一个机智答案背后,都凝聚着无数数据标注员的血汗。
很少有人关注标注员,也很少有人深究他们的工作。然而,标注员是AI产业链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他们一次次枯燥、乏味的工作后,AI模型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群人有不同的工资和待遇,共同点是重复着同一份机械、辛劳的工作。他们就是AI时代的流水线工人。
近日,谷歌一份内部文件曝光。文件显示,Bard的标注员要在3分钟内审阅、标注完Bard的回答。这些数以千计的外包工,在deadline重压之下吃力地阅读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专业文字,一个小时挣14美元。
“人们感到害怕、压力大、挣得太少,而且完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一位外包标注员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
数量上百万的标注员遍布全球,很多都是外包工,在零工经济中赚取微薄的薪水。他们参与每一轮AI浪潮,又离台前光鲜性感的故事极其遥远。行业人士为ChatGPT和大模型将如何革新世界侃侃而谈,而这群标注员生活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仍然“隐身”,甚至生存状况更糟糕。
大战之下的小兵
谷歌正处于久违的危机中。在生成式AI竞赛中,谷歌已然落后于OpenAI。
被颠覆式创新扔到大潮之后的恐惧笼罩谷歌,以至于内部一度发布极其罕见的红色警报(red code )。CEO Sundar Pichai亲自上阵,全权负责AI业务。
在2月季度财报的电话会议上,Pichai告诉投资者:“接下来你们会很快看到谷歌的动作。”
接着,它们匆忙推出聊天机器人Bard,5月又发布了大语言模型PaLM 2。
谷歌急迫地上马新项目,对Bard迭代心急如焚,最终的结果就是压力转移到最底层的数据标注员身上。
有很多个谷歌的合同工说,自从谷歌开始加入AI军备竞赛,他们的工作几何增长,内容也更复杂。这群标注员要处理药物剂量说明和法律文书等等专业文件,时间只给了3分钟,而他们根本没有经过相关知识的培训。
这种有时间限制,又要求精准的工作让人一直神经紧绷。标注员们的劳动伴随着恐惧,当然会影响工作质量。在一份员工提交的报告中,他们写道:如果一直要求他们这样求快,Bard会变成一个危险和充斥着错误信息的产品。
然而,在白热化的竞争中,谷歌无暇顾及数据标注员的感受。他们受雇于AI数据训练公司澳鹏(Appen)和埃森哲,和谷歌切身利益没有太大关系。
AI是个彻头彻尾的全球化产业。澳鹏的正式员工只有1600人左右,而外包员工数量高达上百万。这家位于澳大利亚悉尼郊区的公司伴随AI行业崛起成长为明星,一年收入6亿澳元。
可以预想,这一次生成式AI的狂欢会催生对标注员更庞大的需求,澳鹏也会从中分得更多利润。
只是,无论ChatGPT迭代多少代,硅谷大厂市值上涨多少倍,最底层的标注员不会得到太多好处。
我们可能摆脱标注么?
标注员的工作是纯粹的人类劳动。他们要比较两则新闻,评估哪条新闻相关性更高。他们也要判断AI给出的答案中有没有“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事实性错误。标注员们都有本守则,会从6个角度指导他们做出判断。
以目前AI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离开真人训练。AI标注其实就是不断地动用人类主观性做出常识判断。
AI行业其实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即便在大模型时代也是如此。
国家之间发展不平等的现状客观存在,所有劳动密集型行业要获得超额利润,必须全球分工。
对当地人来说,这种全球分工其实不是坏事。OpenAI合作的外包公司Sama总部虽然位于旧金山,但它的员工来自乌干达、肯尼亚和外包大国印度。在肯尼亚,这些标注员工的工资为每个月2.1万肯尼亚先令(约合1158元),算当地普通工人的平均水平,而且坐办公室,不用做体力活。
SAMA公司员工,图片来自官网

澳鹏这样的公司会很精明地将工资定在最低工资基准以上,而且还会给一个月70美元的奖金。这对当地人来说是笔不错的收入。
在加尔各答郊区,穆斯林女性因为全球分工获得了工作机会。她们给亚马逊、微软、eBay等等训练AR算法和自动驾驶数据。
一些中国年轻人则很欢迎这样的工作。在贵阳市百鸟河数字小镇,数字标准员中会有刚从高职学校毕业的学生,一个月挣1500元。比起送外卖、当服务员,他们其实更喜欢坐在办公室训练AI。
作者项飚曾经很客观地评估过这种共生关系:“由于IT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额外的劳动力储备,该行业或许根本无法快速发展,由此无法向当地工人提供现有的就业机会。”AI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廉价标注员,而标注员们也需要这份门槛不高的工作维生。他们从来不是受害者,也不是需要人同情的弱者,而是一群努力、勤奋工作的普通人。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将低工资、高压力的工作合理化。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也不是压榨标注工人的借口。即便只是自私地为了AI学习数据的质量,这些吝啬的科技公司也应该给标注工人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环境。
AI催生了明星公司、百万富翁,它还将改变各行各业,产生难以想象的收益。只是,这些宏大的愿景和坐在乌干达办公室埋头苦干的标注员无关。当某一天,AI进化到不需要标注员时,这群从来不被承认的功臣又会被毫不留情地扫去角落。
“我告诉我的朋友和家人,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公司的工程师就像人工智能婴儿的亲生父母和私人教师,而我就是清扫他们的育婴房并给他们洗衣服的女佣之一。”一位标注工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
或许,即便我们不可能短期内改变经济、知识结构的区域不平等,起码可以看见他们,衷心认可他们的价值,承认他们在AI时代的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