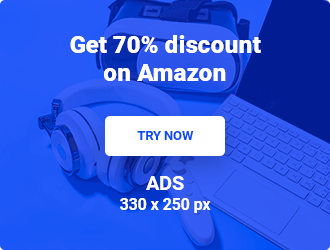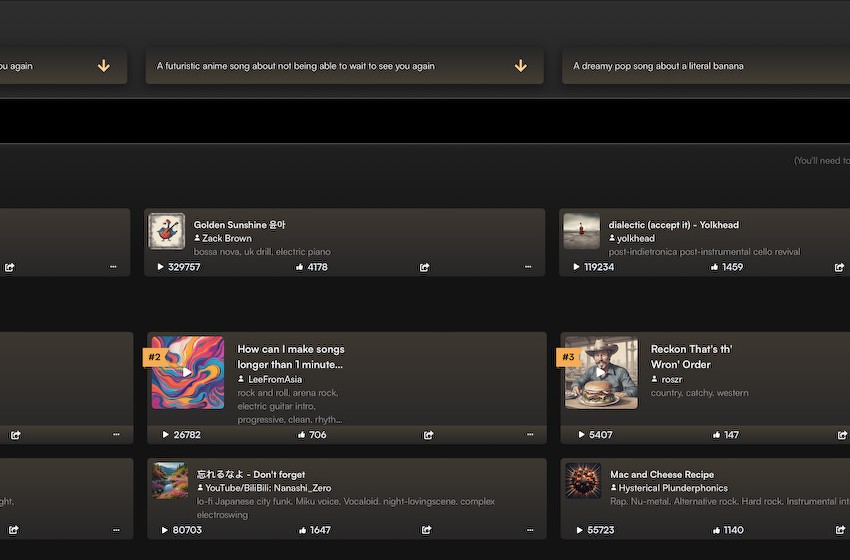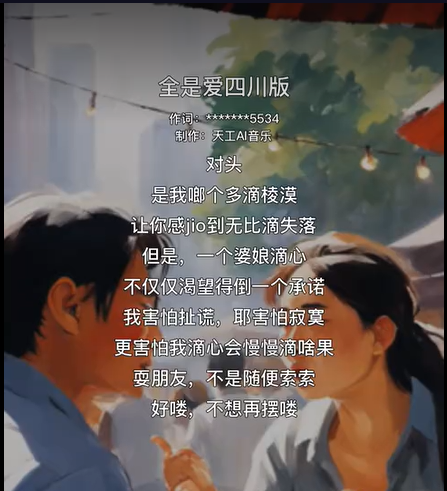公共叙事退潮了吗?私人故事向哪里去?来自FIRST影展的疑问
界面新闻记者 |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昨晚在西宁闭幕,本届主竞赛共有13部剧情长片、5部纪录长片入围。最终,秦天导演的作品《但愿人长久》获得最佳剧情长片,《漫漫长日》导演王子川当选最佳导演,《巢》获得最佳纪录片奖。
“家庭、婚姻生活、情感关系构成了大部分影片的核心叙事……个体表达在不断受限的外部环境下,影片内外传递出某种关照现实的困顿。”本届FIRST的评审寄语如此评价入围的竞赛作品们。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青年影展,FIRST的入围片单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华语青年电影人们的创作生态:他们在关心什么?是冒犯还是固守?他们的困顿于何处?

FIRST青年电影展纪念逝世导演万玛才旦
01 故乡主题:城市影像增多,方言成为“杀器”
《但愿人长久》的导演秦天在返场谈里谈到了他做导演前卖烧烤的经历,“我开了烧烤店之后,才知道市场上你可以选到五十年、四十年或者三十年的冻肉,它们的价格都是什么样的。”
秦天大学时读经济学,为了拍电影回到成都老家,干过游泳救生员、闪送、烧烤、网约车司机……他从这些经历里吸收养料,并写进一个个剧本里。这部电影是他导演的第一部长片,也是今年主竞赛单元的FIRST最佳剧情长片。
《但愿人长久》描绘了三代女性群像。从四川县城来到成都打拼的夏蝉在城市寻求栖身之地,试图建造新的故乡。秦天以迁徙与故土作为故事主线,升学择校、城乡差距、代际隔阂等社会问题交织其中,以车流和高楼呈现成都景观,穿插着被拆迁的老房子、外婆做的叶儿耙、成都市井小巷等画面。秦天希望在电影中探讨城市化进程,及其带来或主动或被动的迁徙。“2010年之后,我开始想,什么样的人是更具有当代性的?从迁徙的角度来看,是女性,她们经历过身份、地位与处境的剧变,所以我选择了女性作为视点。”

在历届FIRST入围片单中,故乡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本届许多作品都呈现了对于故土与身份的代际性认知,以及出走后再次凝视故土的复杂情绪,从家庭到校园,从乡村到城市。
在《乘船而去》里,离乡工作的子女回村照顾母亲时,不断发现母亲的秘密,也逐渐失去与故乡最后的连接;位于山东省南部的“苍山”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地名,也是导演张帆的故乡,他的首作《苍山》讲述的是逃避过往的小妹在上海做家政工,后来又重新回到故乡苍山的故事。
北方依旧苍凉破败,南方仍然暧昧潮湿,乡镇是最多创作者热衷的场景,但城市影像也比以往更受关注。在采访中,FIRST影展创始人宋文提到:“早期我们的作者电影比较聚焦在讲乡村生活、或者城中村的困境,到最近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低成本的、关注城市人家庭关系、自身困境的作品越来越多。从2019年的《春江水暖》开始,后来又有了《雨打芭蕉》这些作品。”
故土关系外化的另一个体现是方言的运用。短片预审评委、影评人子戈说,“我看了七百多部短片,方言创作的有一百多部。”《军军》里的山西方言,《去马厂》里河南人当着北京人说的普通话,背着北京人说的老家话,《但愿人长久》里“真正的成都人才不会说普通话”。当方言成为作者电影的一大杀器,创作者们需要持续思考的是,方言如何延宕影像意义,而不是沦为刻板景观的辅助?怎样避免方言简化为身份符号的表达?当方言常与大量文学性表达夹杂时——如网友评论,十部文艺片九部要读诗——如何避免文本语言威胁视听,不使影像成为文本的图解?

02 女性影像:私密是否有可能抵达公共
“我觉得整体来看就是表达的收缩,大多数电影都是朝向个体、家庭,其中带有无奈感的和解。”在本届FIRST关注女性影像的FIRST FRAME主题论坛中,学者戴锦华如此评价这次评选的感受。
今年FIRST参赛影片中,女性导演占比31%,是影展历年最高的一年。本届FIRST FRAME单元入围的影片涉及中产阶级家庭、身体的探索、不同年龄层女性的困境,关于底层女性、边缘群体的影像相对较少。在女性影像涌现之时,我们或许需要思考,如何避免题材趋同、观点盖过内容,如何在自身经验范围之外,看到更广阔的女性群体处境。
《这个女人》是FIRST FRAME单元的年度影像——一个三十五岁的普通女人,在疫情失去工作后回老家寻找出路,在各种亲密关系中游走探索。这是一部虚实交融的伪纪录片,主角在影片最开始直视摄影机镜头如同纪录片访谈,后来又进入到标准剧情片情境中,引诱观影者猜测她的丈夫与情人到底是谁,最后嘲弄了所有人的预期,推翻看似流畅存在的现实。

入围片单中的私影像创作数量突出,许多影片都回到了单一空间内的制作模式,或因疫情导致行动受阻,也或因制片预算有限。但这些电影仍然在受限的空间中发挥出了创造力,比如《长谈》《试镜》等作品。
《试镜》中,两位女主角间进行了漫长深切的对话。这是一部带有自传属性的电影,两位女主角似乎是导演曹冼将自己一分为二的两个镜面——一位导演,一位演员,试镜的女导演在最后又变成了一个“被试镜”的人,开始讲述自己的伤痛。映后评价两极分明,戴锦华认为导演止于把个人生命的创痛停留在独白形式,“很多优秀的青年创作者存在的问题,是我就想把作品拍出来,不知道拍给谁,作品就变成了独白,而不是讲述,不是‘我说给你听’。”然而,在电影返场谈中,有数位观众表示对电影中二位女性间绵长细腻的对话感同身受。

戴锦华还提到了自己的一个观察,如今整体的电影创作都呈现出向内的收缩性——然而私密影像一定次于公共表达吗?这二者一定是二元对立的吗?或许更重要的,是女性电影如何挑战影史中传统的抵达公共的方式,让私人影像、私人经验也能够走向更广阔的意义 。戴锦华说,“现在的问题不是重新用当年的方式去表达公共议题,拒绝私密问题,而是如何让私密成为一个抵达公共性的路径。每个创作者应该有一点反思或者抽离,试试再换一下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位置,看见一些不一样的、比如不同阶层的生活样态的人。”
03 纪录片:社会议题退场,家庭影像突出
电影《巢》获得了这届FIRST的最佳纪录片奖。八年前,导演秦潇然在一次放映会上遇到了《巢》的拍摄对象房君睿——三十岁,想做文物修复,同父母蜗居在静安寺30平米老房子的人。在最开始,秦潇然只是想拍一部关于理想的短片,但她没料到的是,自己从此进入了一家人的痛苦纠葛,镜头也成了他们倾诉内心痛苦的出口,随着拍摄时间的延长,勾连出了越来越多的时代记忆。
在影片后半部分,秦潇然开始怀疑自己,原本作为局外观察者的她,声音几次都出现在了电影里:“我拍这些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她一再问道。电影映后,导演秦潇然回忆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有时觉得自己就像房君睿,拿着他要修复的碗,在黑漆漆的房间里不知道怎么办。”
《巢》最终呈现的文本议题是复杂的,除了导演自言的理想失落,也关于物质与精神生活、纪录片与拍摄者、代际关系,以及对民主空间的理解。

本届FIRST纪录片单元共有五部长片入围,三部涉及家庭、代际与情感困境。观众票选中评分最高的《风起前的蒲公英》,关注的是一所北京进城务工子女中学因大兴机场修建需要搬迁,学校合唱团面临离别的故事。虽然涉及流动儿童、城市扩张与拆迁等议题,但影片绝大多数篇幅都聚焦于合唱团的苦乐悲喜。《金鸡冠的公鸡》则聚焦母女关系,女儿自杀后,母亲在痛苦中挣扎,为了弥补缺憾,她又养育了一个女儿,女儿青春叛逆期难以相处,母亲则困于黑暗的隧道中。
本次纪录片的预审评委黎小锋的作品曾在2016年的FIRST获得最佳纪录片奖,对比两届入围片单,他评价:“那一年的入围片创作手法大都偏观察型,社会议题性更强。《黄星绿地满天红》观察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左翼群体,我们做的《昨日狂想曲》则是关于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大学。这几年很明显的趋势是私影像、家庭影像在增加。”另一位预审评审沈燕妮则向界面文化记者提到,在五十多部报名作品里,只有2-3部作品直接或间接与疫情有关。

青年影展为独立纪录片提供了些许被看见的机会,FIRST纪录片单元曾出现了《囚》《四个春天》《棒!少年》等口碑颇高的作品,而诸多影评人对这届FIRST的共识是一个纪录片“小年”。宋文说:“我认为这几年都是小年,纪录片作品比较少。”
FIRST纪录片实验室执委会委员张新伟也向界面文化记者谈到了纪录片导演的困境,“能上院线的纪录片非常少。独立纪录片此前有几年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比如《人生一串》《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网络平台火了,平台就会去委托作者型导演拍片。最近几年这样的机会少了,纪录片导演生存更加艰难了。”宋文补充道,从全世界的范畴内来看,能够在主流院线里广泛传播、得到很好票房的纪录片都不多。“我们不能陷入到那样的语境里,但是我们应该创造出更多传播的渠道,比如大学的图书馆、学术场地,应该给纪录片更多的放映和讨论机会。”
(本文图片均来自FIRST青年电影展主办方,经授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