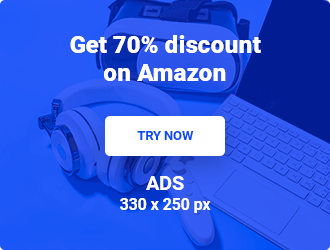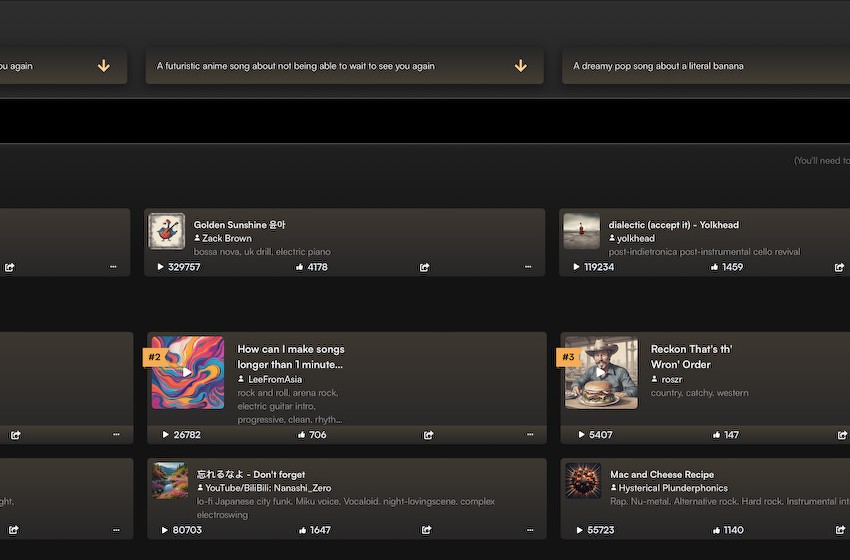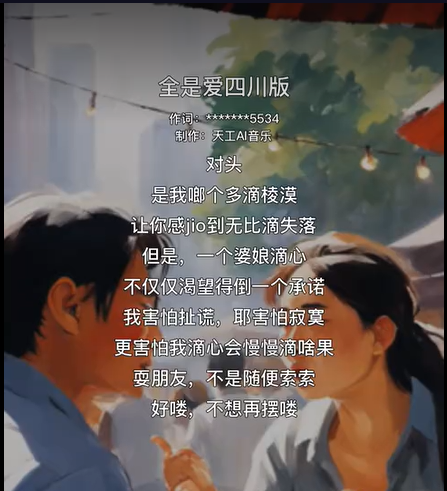龚金平等:影视艺术要绷紧历史观这根弦
作者:龚金平 艾青 周仲谋 高佳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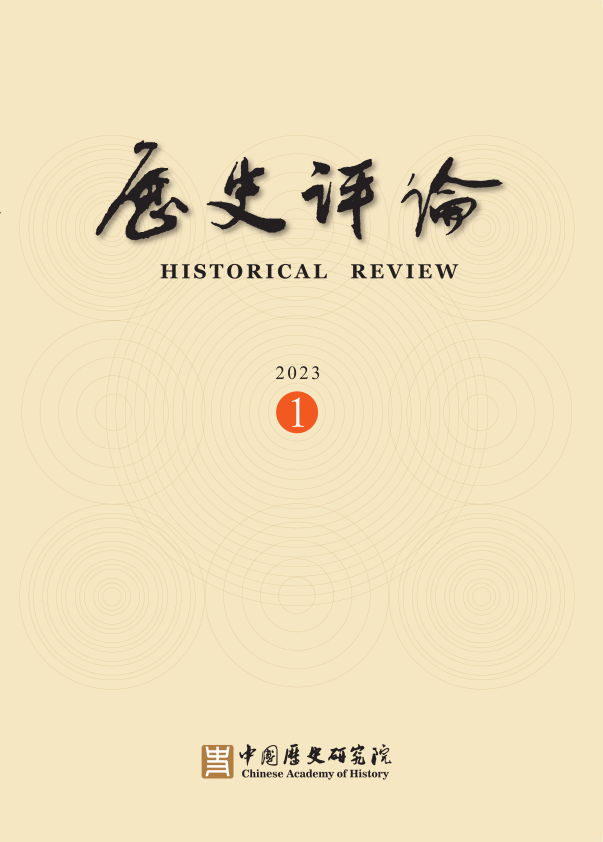
近十年来,影视艺术领域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品,在真实呈现历史、讲好历史故事方面广受赞誉。不过,同样是讲述历史,有些作品的艺术处理却引发不同解读。就历史观来说,影视创作应该如何把握艺术真实与历史事实间的尺度?本刊编辑部邀请四位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历史能否仅仅当作素材来使用?
周仲谋:最近十年来,中国影视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2021年全国银幕数量突破8万块,自2016年以来连续6年银幕总数保持世界第一,稳居全球最大电影市场宝座。国内影视艺术依据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创作出一系列历史和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如《长津湖》《狙击手》《1921》《觉醒年代》《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山海情》《大江大河》等,受到广大观众喜爱和好评,收获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外影视剧中也不乏好的作品。然而,受消费文化影响,一些影视作品因过度追逐商业化和娱乐化,放松了历史观这根弦,在题材运用、叙事手法、人物塑造、文化传播等方面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加以讨论。
影视创作经常涉及历史题材。影视与历史的关系是怎样的?历史在影视创作中通常会以什么方式“出场”呢?龚老师,请您谈一下。
龚金平:宽泛地说,电影以及其他叙事艺术的题材有三类:过去(历史)、现实与未来。身处中国这种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创作者从历史中寻找题材资源或者创作灵感,几乎是下意识的选择。中国古代历史题材的影片层出不穷,其中不乏艺术或市场力作。近年来,弘扬主旋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更是群星闪耀。
这些影片的创作目标并不一致,历史的“出场”方式和呈现风貌也存在巨大差异:有些影片青睐于传奇性,因而尽力凸显历史的曲折复杂或者惊险色彩。有些影片挖掘历史的思想教育意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但还有些影片,只钟情于历史本身的话题度,希望借此摆脱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诸多限制,这类影片大多以一种游戏姿态,把不同的故事、话语拼贴在一起,并对一些历史事件和电影片段进行戏仿,使自身成为受消费文化影响的狂欢化文本。
艾 青:您能结合具体作品,深入分析一下“以游戏姿态对历史进行拼贴、戏仿”的现象吗?
龚金平:比如2014年上映的《一步之遥》。影片取材于1920年轰动上海滩的“阎瑞生杀害妓女案”和1921年拍摄的电影《阎瑞生》,但作了彻底的“翻案化”改写。命案的基本情况是:洋行买办阎瑞生嗜赌好嫖、挥霍无度,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阎瑞生偶遇名妓王莲英,见她打扮得珠光宝气,遂准备谋财害命。阎瑞生伙同另外两人,驾车假意邀请王莲英外出兜风,将她勒毙于上海徐家汇麦田,抢走其佩戴的贵重首饰后畏罪潜逃。后几经周折,阎瑞生和同伙归案伏法。由于该案在当时影响较大,投机者从中看到商机,很快拍摄成以案情为蓝本的电影《阎瑞生》,上映后颇为轰动。阎瑞生案从新闻报道,到戏剧、戏曲、电影的搬演以及演义,当时可谓热闹非凡。虽然20世纪20年代各种艺术样式对于阎瑞生案的表现确实格调不高,但这个案件的性质是明确的,基本事实和过程也无可争辩。
《一步之遥》却“标新立异”,对案件进行令人错愕的想象和重构:阎瑞生和王莲英情投意合,阎瑞生根本就没有杀害王莲英,而是两人吸食鸦片之后神智错乱,王莲英因车祸而丧生。影片谴责民众和社会舆论不关心案件的真相,只是根据个人想象和一己私利,将阎瑞生丑化成十恶不赦的坏蛋。影片用一种戏谑、调侃和黑色幽默的方式让观众看到,马走日(以阎瑞生为原型)被诬为杀人犯之后,媒体、文明戏演员、法租界、军阀都没有澄清事实的动力,而是热衷于在这个案件中注入各方利益,或者体现各自的心机。这样,马走日杀人案就成了一个引子或者刺激事件,影片试图借此折射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人心,并让观众意识到,人们所了解的“历史”可能是被利益和观念等因素绑架、歪曲而改写成的。影片让人物不止一次提及:今天,我们见证了历史!今天,我们创造了历史!今天,我们都是历史的参与者!言外之意是,人们即使身在“历史”中,也可能将自己臆想的事实流传下去,还沾沾自喜于自己见证或创造了“历史”。
影片因此陷入巨大的道义困境:它在强调“历史”可能被人涂抹而离题万里时,却在为一个真正的杀人犯张目。这样,影片不仅没有为观众提供对于历史的重新审视或者现场还原,反而将一宗历史公案进行翻案改写,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浪漫化甚至英雄化塑造,这无论如何都称不上一种客观公正的历史立场。影片试图表现一种新的历史态度和观念,采用后现代的戏仿、拼贴、杂糅手法,以嬉笑怒骂的方式,举重若轻般对人性的自私、肤浅、卑劣进行鞭挞与讽刺,并高歌荒诞年代的理想主义坚守,确实具有一定讽刺意味和批判锋芒。但是,用歪曲历史的方式,去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人心,进而标榜创作者的历史观,这种做法本身就存在问题。
高 佳:龚老师,影视创作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处理历史题材呢?
龚金平:在市场化运作中,许多影视公司面临资金回收压力,有时不免迎合某些观众的审美品位甚至消费心理。这种情况下,影视作品如何讲述历史、能否用影像更好地呈现历史,确实是个重要问题。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究竟应该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还是“演义”历史、消费历史,这看起来是创作者的自由,或者是市场的自我选择,但实际上也关系到观众接受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既然作品的主要内容涉及历史,观众对于史实就会有基本的立场和观点。作品如果对历史进行随意、轻浮的裁减或捏造,就是对观众的极不尊重。创作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时,创作者无论出于艺术动机还是商业目的,都应该基于正确的历史观,以恰当的方式还原历史情境,捕捉历史的脉搏和气息,描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人心。在此基础上,影视艺术才能进行个性化的创造与发挥,为后人提供观照历史的不同角度,进而产生不一样的情感触动或者思想启示。这才是一种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创作理念,也是我们对于历史应遵循的基本态度。
如何呈现历史发展的主动力?
周仲谋: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不仅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历史、尊重历史,还应该运用恰当的叙事手法和技巧,讲好历史故事,呈现历史发展的主动力。艾老师,您能不能结合具体影片来谈一谈?
艾青:好的,那我就结合2021年上映的电影《兰心大剧院》谈一谈。这部电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改编自华人作家虹影的小说《上海之死》和日本作家横光利一的小说《上海》。影片在叙事上还是挺有特点的,创作者颇费周折地建立起一个“戏中戏”的套层叙事结构。一方面,影片沿用了原著《上海之死》的外在框架: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周,著名女演员于堇应“旧爱”谭呐导演之邀从香港返回上海,在兰心大剧院排练出演话剧《狐步上海》。于是,“于堇回沪究竟为了什么”成为开篇抛出的悬念,表面上于堇是为了营救关押在汪伪76号的前夫倪则仁,而随着线性时间的叙事推进,她的真实目的浮出水面。另一方面,里层的“戏”《狐步上海》被改名为《礼拜六小说》,嫁接了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小说《上海》中关于“五卅运动”的故事背景,而戏里于堇所扮演的女工秋兰与谭呐所扮演的日本侨民参木,除了保留原来的姓名身分外,人物之间的戏剧情节几乎脱离了《上海》。
龚金平: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觉得“戏中戏”套层叙事结构使影片的人物和故事变得复杂了,剧情在“戏”里“戏”外跳来跳去,有点像谍战片的悬疑叙事,但又缺乏清晰的逻辑结构。
艾青:影片确实存在这样的不足,人物群像复杂多变,话剧舞台与生活场景的边界模糊难辨。影片并不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逻辑的建构上多着笔墨。前夫倪则仁为什么一定要被纳入计划?于堇对此是什么样的情感态度?一个远离日军大本营和决策层的低阶情报官古谷三郎,凭什么能接触到偷袭珍珠港这种高度机密计划,又为何会被派往与作战计划无紧密联系的上海传递密电码?影片对这些均未清晰交代,只提供了相对感性零散的人物关系的截面,“双面镜计划”的具体执行过程也显得很随意。
尽管影片采用了谍战类型片的悬疑叙事手法,但创作者将兴趣更多放在互文形式的艺术实验上。例如,“戏中戏”话剧《礼拜六小说》在电影中的表现形式是“软性”的谈情说爱,主题却是一部左翼作品,回望1925年的五卅反帝运动历史,有意识制造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与左翼的文学对话,以期同于堇的多重身分迷宫一起构成对“孤岛”时期上海历史时局的叙事回应。然而,《礼拜六小说》这部话剧既不是迎合市民欣赏趣味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也没有发动群众进行抗争的启蒙意图,从而造成“去历史化”的某种荒诞性。由于忽略故事逻辑、人物情感与主题表达的承载,《兰心大剧院》中繁复的异质性元素在密集又迷幻的电影语言装饰下成为漂浮的能指,历史在虚实变幻与意义空缺中被消解为碎片化幻象,历史发展的主动力也变得模糊暧昧起来。
高佳:影片似乎以女主人公于堇的情欲来推动“历史”叙事。
艾青:影片试图表现多重政治纠葛下一个女性的情感和选择,并设计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节,但过于强调女主人公的情感爱欲,甚至让它成为推动故事发展和历史事件走向的重要力量。影片结尾处,用特写镜头展示《少年维特之烦恼》初版本扉页上尼采的话——人们最终爱的是欲望本身,而非自己渴求的东西。这句话可以视作对女主人公行为动机的注释。影片夸大于堇的神秘感和魅惑力,让她游刃有余地周旋于种种阴谋和不同政治身分的人物之间。军统特工、文艺女青年白玫甘愿充当于堇的舞台替身;日本情报官古谷三郎受于堇催眠及性暗示影响,吐露了密电码信息;枪战中,于堇如复仇女神般开启强大的战斗力,击毙了大剧院内外的所有敌人;最后于堇又为了与谭呐一起离开,赴死般前往船坞酒吧。
影片以于堇对乱世与生命的主观感受,左右着整体的叙事布局,其背后是泛欲望化的历史叙述观念。而于堇死亡的悲剧性与牺牲感又因舞台内外空间的自由切换而被悬置,化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幻象。这也影响到影片的审美接受与价值认同,特别是片尾仅凭借一封信来揭晓情报信息,缺少人物情感逻辑的铺叙,显得突兀。于堇向她的养父兼上级休伯特传递假密电码的缘由,在电影中并未交代清楚,甚至原小说《上海之死》中那句“因为我不得不帮助中国”也被删去,导致全片在价值表达上颇为混乱,难以获得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感认同与心理共鸣。
周仲谋:把情欲作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显然是不合适的。您认为,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视创作应该注意什么?
艾青:抗战历史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共御外辱、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共同记忆,一直是影视创作的重要题材来源。无论是选用先锋实验的还是商业类型的叙事手法,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呈现历史发展的主动力和大趋势,而不是陷入解构历史、歪曲历史的误区。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视创作,决不能把历史和价值虚无化,更不能贬低和消解伟大的抗战精神、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削弱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当下影视创作需要格外注意和深思的。
如何塑造历史上的英雄形象?
周仲谋:龚老师和艾老师分别从题材处理、叙事手法等方面发表了精彩见解。下面我想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谈一些粗浅认识。
近年来,影视作品中塑造了不少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如《战狼》系列中的冷锋、《湄公河行动》中的高刚和方新武、《长津湖》中以伍家兄弟为代表的志愿军将士、《万里归途》中的外交官宗大伟,等等。这些英雄形象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同时彰显出难得的优秀品质,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为民,奉献牺牲,让广大观众深深感动。然而,有一些影视作品在塑造英雄形象时,放松了历史观这根弦,竟然把流氓和土匪等人物加以美化,将他们刻画成“有情有义”、“善恶必报”的民间英雄,而对真正的历史英雄或者有所回避,或者加以歪曲。
龚金平:我觉得2016年上映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能说明一些问题。影片的主人公陆先生,是以杜月笙为原型的,情节上刻意凸显他的仗义助人、优雅从容、讲原则、恩怨分明,把该人物塑造得可亲、可敬,甚至有些可爱。影片风格上带有鲜明的实验性和唯美色彩,一些观众可能被其独特风格吸引,认为整部影片还挺好看,而容易忽视人物形象背后的价值颠倒。
周仲谋:确实如此。影片的形式实验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缺失。影片表面上讲述了抗战前后发生的故事,实际上对上海革命历史有所歪曲。例如开头部分,上海滩风云人物陆先生处理一起罢工事件,让人砍了罢工组织者周先生情妇的手,逼他说出秘密,又派人将周先生押送到野外活埋。在这段情节中,影片强化了陆先生的处世原则,凸显他对上海的“热爱”。他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给周先生送去翡翠玉镯,约到茶楼谈判。因周先生收了礼物又当面撒谎,拒不配合,陆先生才采取强硬手段迫其就范。这样的情节设计,把陆先生对事件的处理呈现为正义之举,却抹黑和歪曲了罢工领导者形象。该事件其实是有历史原型的,即1927年杜月笙杀害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汪寿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思想进步,为人正直,牺牲时年仅26岁。影片却将罢工领导者周先生丑化成一个包养情人、贪婪狡黠、胆小怕死的卑劣之徒,借陆先生之口把工人运动说成是被别有用心者胁迫,是对上海正常秩序的破坏。
然而,对上海近现代历史稍有了解的观众,都知道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所作所为。电影要将昔日的流氓大亨变为“浪漫英雄”,就不得不在形式风格和叙事技巧上多花些心思。影片着力宣扬陆先生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所谓“爱国精神”,为复仇先后杀死日本军官、汉奸“二哥”和高级间谍渡部。但这样的“英雄形象”是建立在碎片化叙事基础上的,重组的时间和碎片化的叙事,恰恰掩盖了陆先生识人不明、刚愎自用、把他人当棋子的本性。试想,日本间谍渡部潜伏上海多年,成了陆先生的妹夫,陆先生竟丝毫没有察觉其真实身分。渡部半路枪杀司机并绑架小六囚禁数年,仅一句“司机说要在苏州走亲戚”就蒙混过去,而司机三年未归,陆先生却毫不起疑,岂不是过于糊涂吗?陆先生让五姨太去刺杀汉奸,打死大外甥逼“日本妹夫”认罪,派人砍掉周先生情妇的手,都是以牺牲无辜弱者来达到目的。
影片渲染陆先生的“处世哲学”,突出他仗义助人、帮助弱者的品质。但从剧情上看,陆先生固然有替小六求情、放她离开上海的行为,但背后未尝没有自己的隐秘欲望。陆先生帮助了电影明星吴小姐,但这份人情是要还的,在陆先生和王妈等人的软硬兼施下,吴小姐被迫接受戴先生(人物原型为戴笠)的包养。实际上,陆先生绝非同情弱者的慈悲之人,更不是为国为民的英雄,而是乱世中把他人当工具来实现个人欲望的奸雄,他身上有阴狠、残忍、自私的一面。只是在影片刻意为之的时间顺序和叙事技巧下,该人物的缺陷被巧妙掩盖,很难被观众察觉。
高佳:周老师,影视作品在塑造历史英雄形象时,最应该注意什么?
周仲谋:要以史实为依据,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切忌为了“出新”而罔顾史实,把已有公论的反面人物塑造成“另类英雄”,或者有意塑造“反英雄”形象。对历史英雄形象的塑造,一方面要表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呈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形象特点,另一方面要突出崇高感,凸显英雄人物身上的优秀品质,以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引领观众。
“他者”的历史能否随意虚构?
周仲谋:近年来,中国元素成为西方影视创作的新灵感,这对传播中国文化有积极的一面。但有的西方影视作品,虽然取材于中国故事,却随意虚构甚至歪曲中国历史。美国奈飞(Netflix)公司2014年出品的《马可·波罗》就存在这种情况。
高佳:把马可·波罗漫游中国的故事改编成影视剧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本来应该可以加深世界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认识。然而,历史观的严重局限,导致这部剧存在诸多缺陷。
这部剧最突出的问题是无视历史真相,虚构中国宋元历史,歪曲或丑化相关人物。在《马可·波罗行纪》的描述中,忽必烈是一个中等身材、不高不矮、四肢匀称、整体协调的人,面貌清秀,有时红光满面。他博学儒雅,对外国宗教很开明,对来自威尼斯的商人也很友善。而剧中的忽必烈,则被塑造成体型臃肿、喜怒无常、荒淫好色、言辞粗鄙的暴君。南宋方面,“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宋末三杰在剧中被抹去,朝廷中文人气节荡然无存。宋元繁荣的市民文化和市井生活图景极少呈现,元大都的宏伟壮丽也不见踪影,处处笼罩阴森恐怖、暴力血腥的气息。
该剧无意于真实表现宋元历史和文化,也无意于真正促进文化交流,而是热衷于猎奇和窥视,试图以外邦人视角透视宋元宫廷秘史及政治斗争。在这样的主观意图和情节预设下,该剧刻意渲染宫廷生活的奢靡荒淫、尔虞我诈,凸显色情和暴力元素,甚至篡改历史,让当时已去世的阿里不哥“复活”与忽必烈争夺皇帝之位,并让史书中早逝的贾贵妃成为潜伏于蒙古后宫的美女间谍,以此迎合西方观众对东方的“他者”想象。
艾青:萨义德的《东方学》认为,西方长期以来将自身视为中心,带着优越感去想象、虚构东方,甚至把东方“妖魔化”。该剧对中国宋元历史的篡改与歪曲,就有西方中心主义和自大心理作祟的成分。
高佳:这部剧在“妖魔化”东方的同时,还极力打造“西方神话”,把马可·波罗塑造成西方式“超级英雄”。该人物不仅相貌英俊,而且睿智勇敢。他慧眼如炬,揭穿不少阴谋,既帮助忽必烈处理内患,也为攻陷襄阳立下大功。他凭聪明才智解决了自身危机,还赢得几位女性青睐。该剧对马可·波罗形象的处理,既不符合中国历史记载,也不符合《马可·波罗行纪》的描述,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向壁虚造。
龚金平:这部剧作的传播接受情况似乎也不大好。
高佳:该剧的播出并未达到主创团队所希冀的效果。美国《好莱坞报道者》评价道:这部剧只是一场灾难——如此平庸的作品,随便找一个普通的有线台都能拍出来。《华盛顿邮报》更是直言:这部剧极度缺乏让人看下去的动力和意义,剧情走向和支线都老套古板、毫无新意。很多网友认为这部剧罔顾历史、剧情混乱,整部剧集充斥着西方影视创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与糟糕口碑相伴的是收益惨淡,该公司已取消再拍续集的计划。
周仲谋:这部剧作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了什么经验教训?
高佳:历史剧的艺术魅力在于历史事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剧应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深度还原该时期风土人情,力求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无论是对本国历史还是他国历史,都应保持足够的尊重和敬意,这是影视艺术呈现历史的基本底线。
周仲谋:我们把大家比较熟悉的几部影视作品拿来讨论,并不是要作出面面俱到的总体评价,而是想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一些具体问题。希望今天的讨论,能给广大影视艺术工作者、广大观众提供一些参考。我们认为,无论就题材运用来看,还是从叙事方式、人物塑造方面来分析,抑或从传播接受角度来说,影视艺术与历史观之间都存在深刻关联。影视艺术只有绷紧历史观这根弦,才能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