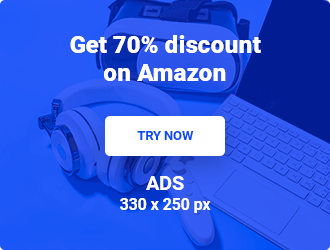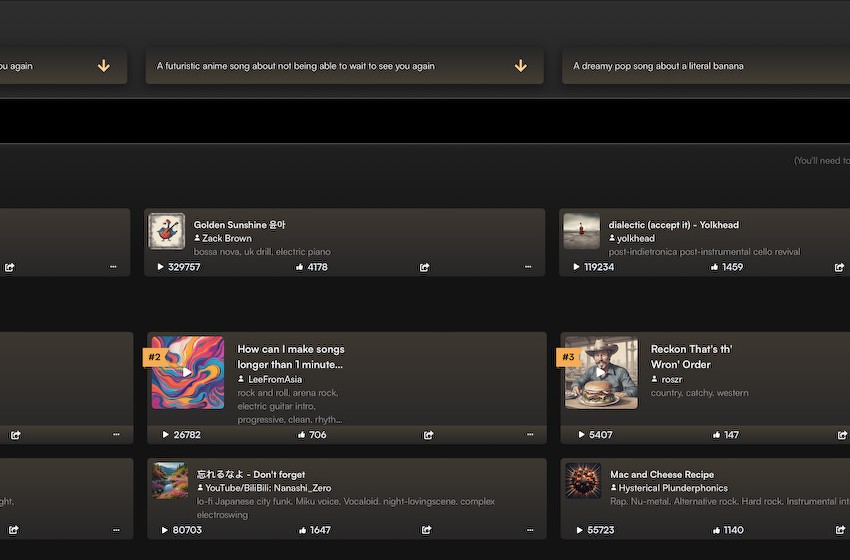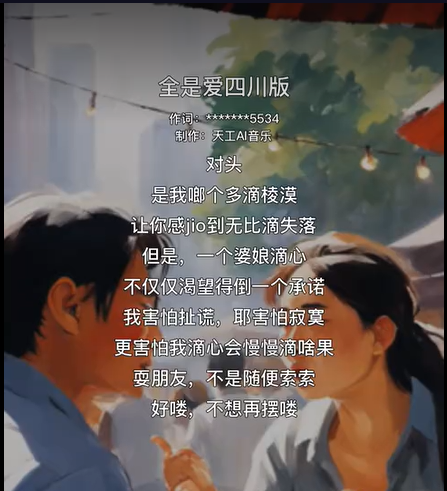林深见鹿 | 来颖燕

电视剧《最好的我们》(2016)剧照
上海的冬天常常湿冷,苦寒的日子并不多。因此,十三四岁那年的寒冬会在记忆的背包上划上一刀。快放寒假时,路过学校花园里的小池塘,水面的冰层粗粝又结实。当时我很兴奋,更显出身边同学的冷静。她说:“冰面下的水还在流淌。”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懵懂岁月里的点滴,如果能抵住时光的侵袭,就会成为今后的谶语。这或许是为什么,每年的高考季会触动大家的共情,默契地回望少年的自己。
中学时代,学校的元旦文艺汇演,是一场重要的释放和告别,高三的学长们准备的节目永远关于离别。小虎队的“放心去飞”,是最贴切的背景音乐。等到自己搬到了高三的教室,好朋友在临别留言本上写道:你这个坏东西,像一列火车,载着一车的好东西就要开走了。记忆的迷宫里,关于青春的一切,苦恼、迷茫甚至怨怼,都会是清晰而美好的存在。
前几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新书分享会,一个在读研究生现场提问,诉说对自己今后何去何从的迷惘。她问自己也问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当时脑子里立刻蹦出弗罗斯特的诗句:“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人本来就是惊奇而不确定的存在,那些岔口,危机四伏,又充满无限可能,所以日子才值得过下去。
于是,弗罗斯特感叹:“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光阴制衡着我们的选择。我们必须不断地面临路口的分岔,选择其中一条,然后再往下继续选择,直至走向密林深处。林深未必能见鹿,也永远没有回头路。
我从小偏科。数感很差,语感是上帝给我开的另一扇门。但我很幸运,遇到一位开明的数学老师。他的普通话很不普通,经常硬性音译沪语。他会说我们要做一个“传良”(善良)的人,也会通知大家一会儿到“露梯”(楼梯)边集合。他自觉在上海滩,数学教得跟他一样好的老师有,比他教得更好的没有了。这话令身处叛逆期的我们也无从反驳。他当时写了一本专门讲解数学解题思路的书,很热销。那时坐我右手边的男生,自视甚高,但对数学老师是真心崇拜。他买了老师的书,下课又追着老师索要签名。回到座位上,他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老师的笔迹,然后工工整整画上了个框。我很诧异:这是干嘛?他解释说这是着重强调的符号,表示尊敬。我说如果老师看到会打你的,他忽然陷入了迷茫。
对于数学的绝对分值永远要低于语文和英语的我,这位教了我们七年的白发苍苍的数学老师从来没有流露过嫌弃的眼神。他会用他的“洋泾浜”跟我说,每科都优秀的学生,以后可能很难真的成功,因为真的成功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是他给我的宝贵的定心丸,给予我继续放肆偏科的勇气。
而我那刚出师范校门不久的语文老师,是沉稳老道的数学老师的参照系,只是他们的骨子里潜有同样的自信和智慧。她时髦而不羁,蹦蹦跳跳是她的走路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延展成不按常理出牌的教学方式。校长因此找过她谈话,但她依然特立独行。她预言我们以后一定会感激她,现在想来这话并不过分。她让我们意识到语文一科并非只能跟限定答案的试卷捆绑,模糊性和开放性才是它的魅力所在。于是,我们被要求隔几周读一本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罗亭》《傲慢与偏见》……这些故事从此轮回在许多个人生瞬间。她会告诉我们《呼啸山庄》要胜过《简·爱》,尽管那时的我们还是更喜欢《简·爱》那悲伤但光明的结局;初一的试卷里,她会要求我们对诗歌的平仄进行判断,尽管这完全无“纲”可依。她出的试题总是没法跟市里其他重点学校同属一个频道,却真实地让我们跟以后的大学学习生活无缝链接。她有时会召集几个学生帮她一起批改试卷,我曾是其中之一。那次期末考她出了一道题:“你能不能根据下面这段作品的风格判断作者是谁?”这样的题型,在多年后我参加中文系硕士面试时往日重现。当然,中学那次的题很少有人能写对答案,记得我看到的一份试卷上,某同学就写了一个字:“能”。我拿给语文老师看,她大笑。但是又没法下笔打叉。
语文老师会要求我们排演名著里的桥段。同样有排演任务的还有政治课。那次政治老师让我们排一场闻一多在演讲后被枪杀的戏。一位女生要演闻一多的夫人,在丈夫被枪杀后哭诉当局的暴政。她全情投入,不断拿手绢抹眼泪抽泣。但作为观众的我们那时还无法领略这个桥段的深意,反而因为她太投入了而出戏了。有人开始笑,最后大家一起哄堂大笑。结果,我们整个班在放学后被留下反省。
这是很严重的惩戒。因为我们学校总是下午三点就放学,即使是在高三那样紧张的岁月里。我们总是被要求早早回家,各干各的。于是,在台下下苦功成了我们学校的传统,但因为没有硬性的要求,一切全凭自己的兴致和精力,所以在高三之前,我们都无知无畏地飞扬着。放学后,会结伴去学校外的小街音像店里淘9块9的卡带,伴着满大街飘荡的张学友的《吻别》或是彭羚的《囚鸟》,把自行车踩得飞快……那年的《戏说乾隆》令同桌着迷以至于在化学课上收集实验中析出的盐粒,说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建个盐帮……
普鲁斯特笔下的马塞尔说:“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乃是那同时萦绕着我们的记忆与感觉这二者之间的某种关系。”往事的重现,必须有非属记忆作用的其他事物的出现,比如味觉、触觉、听觉(博尔赫斯语)。这乱糟糟的一切,让整个青春的记忆毛茸茸的,仿佛是个清醒的梦。直到面临高考需要文理分班时,我们突然意识到,人生的选择题开始一道道横在我们面前。记忆里,从那一刻开始,空气变得凛冽。联考前,以前爱吹萨克斯风的男生在头上绑上交通大学字样的条幅,手握三支铅笔,向东方拜了三拜。他说这是祈福。他后来果然如愿进了心仪的学校。我想,嗯,迷信就是痴迷地相信,看来心诚很要紧。
心诚是因为大家终于开始明确自己的方向。
至于我自己,终于做了逃兵,因为当年有可以提前报考某些高校文科基地班的机会,我想来想去,跷脚多年,还是认清现实,皈依了早就认定的专业吧。隔壁班的数学老师在走廊上遇到我,认真地鼓励我说:“其实你可以再努力一下去高考,努力一下,你的数学可以从110分进步到120分,从120分进步到130分,最高进步到150分。”(当时高考一门主课的满分是150)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但是更坚定了自己的方向。
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否做对了那一刻的人生选择题。或许多年后回望,才能走出局限有所领悟。但是“多年”到底是多少年呢?对于无法踏上的另一条路上的风景,我们永远葆有着好奇和遗憾。
记得中学时代的体育课,有一个特别让人恐惧的项目——越野跑。要越过我们自己的校门口,然后穿行到隔壁的大学校园,再绕回来。漫漫长路,如果认真对待,真的是魔鬼训练。但好在没有体育老师全程陪跑,他只是在终点等我们。这给予了我们充分的“活动”空间。在屡次试错后,我们发现了一堵墙,翻过去,就可以抄一半的近路,足以在另一半的路途上悠悠荡荡,然后体面地抵达终点。很快,其他班的同学也发现了这条被一堵墙遮蔽的近道。很快,因为翻的人太多,墙塌了。再后来,凡是涉事的,都被教导主任叫去了办公室……
但我知道,那时的我们不曾后悔,只是暗地还想要怎样再辟蹊径。这生猛的青春,值得我们用余生致敬——它是在面临密林中的一道道岔口时,即使周围沸反盈天,也会任性,会不问东西的存在。林深见鹿,原来那头鹿,正是我们自己。
作者:来颖燕
编辑:谢 娟
责任编辑:舒 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