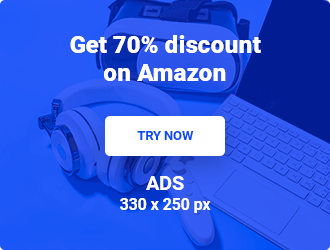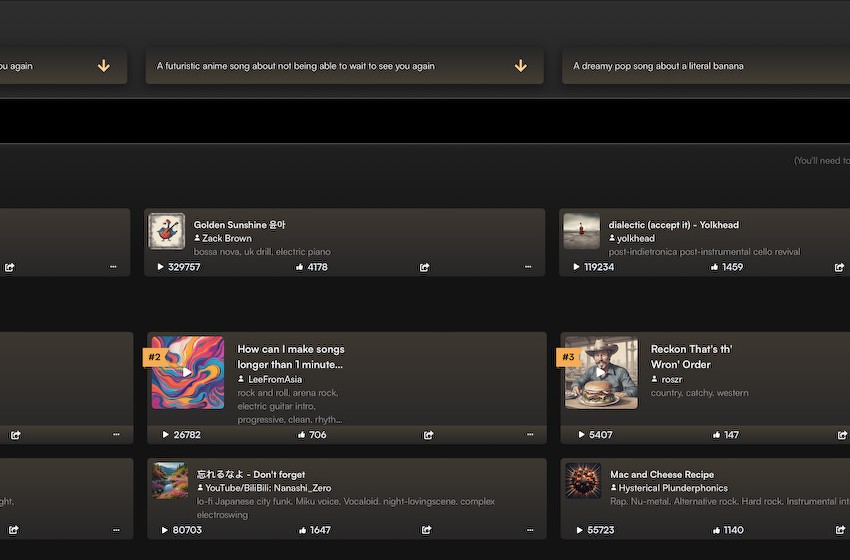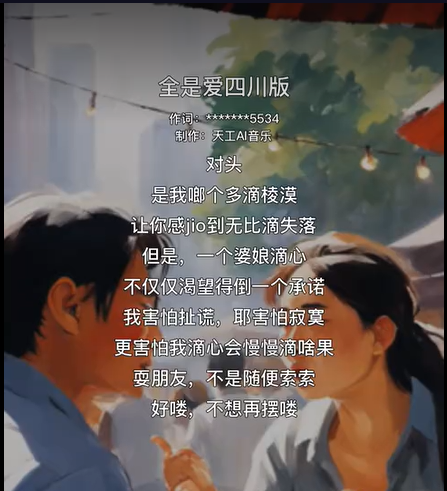一位隐藏在法国电影新浪潮背后的关键人物
作者:Richard Brody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The New Yorker(2023年7月19日)
历史上有许多无名英雄,他们不为人所知的壮举却对公众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让这些人物走出历史的迷雾是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责。海伦·斯科特就是这样一位隐秘的英雄。斯科特是美国电影公关人员,后来成为翻译,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和弗朗索瓦·特吕弗合作撰写的《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
她一生从事电影内外的各种活动,与她深厚的文学素养相得益彰。将斯科特的生平和作品公诸于世的作家是特吕弗的传记作者之一塞奇·图比亚纳,他撰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经过深入研究的斯科特传记《美国朋友》,于2020年出版。图比亚纳还编著了《我的朋友特吕弗和斯科特》一书,这本书收集了斯科特与特吕弗在1960至1965年间的通信,已于今年5月出版。

在这两本尚未翻译成英文的作品中,图比亚纳不仅重构了斯科特的生平故事,还揭示了她在书信中流露的迷人心声。她与特吕弗之间的关系对两人都至关重要。
实际上,特吕弗既和她产生了一段柏拉图式的爱情,也是斯科特的艺术灯塔,为她带来了最深的满足感;她既是特吕弗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主要推动者,也是他心底秘密的分享者。和斯科特一样,特吕弗本质上也是一位文学家,他写给她的信为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出口,这在他大量发表的书信中是绝无仅有的。

海伦·斯科特与特吕弗
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一段轶事。这些书信始于六十年代初,与斯科特在纽约「法国电影办公室」工作的时间相吻合,她在那里推广特吕弗及其法国新浪潮同侪(如让-吕克·戈达尔和阿涅斯·瓦尔达)的电影。这些书信浓缩了新浪潮早期的故事、它为成功所做的努力以及它所面临的敌意。
书信中还包含了大量有关电影发行和评论的细节;导演、演员、技术人员甚至影评人的个性;电影宣传中的实际操作;以及电影成功和导演职业生涯所依赖的微妙关系和奇特机遇。在整个故事中,斯科特和特吕弗的友谊是一部正在创造中的电影史,而她在创造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扮演了隐秘而关键的角色。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斯科特直到四十多岁才开始关注电影。1915 年,斯科特出生在纽约的一对犹太夫妇家中。她的母亲贝茜出生在纽约的一个匈牙利家庭,生下斯科特时还不到 20 岁。她的父亲威廉是来自乌克兰的记者,革命后前往俄国。(1923 年,他带着家人来到巴黎,在那里生活了近十年,1932 年返回美国。海伦对学习没什么兴趣,14 岁就辍学了;在纽约,她在一个隶属于共产党的工会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写传单,经常站在罢工的第一线,面对警察和暴徒的暴力。她告诉法国导演克劳德·德吉弗雷,她认识所有所谓的证人,即沃伦·比蒂1981年拍摄的电影《烽火赤焰万里情》中描述的一群真实的受访者。)

《烽火赤焰万里情》(1981)
她曾与同为工会活动家的弗兰克·斯科特·基南短暂结婚,并在名字中保留了他的姓氏。纳粹德国进攻法国后,一位名叫热纳维耶芙·塔布伊的法国著名记者来到纽约支持抵抗运动;在那里,她聘请了通晓多国语言的斯科特(她还会说俄语和意第绪语)作为助手。
塔布伊声名显赫,人脉广泛,斯科特也加入了塔布伊的名流朋友圈(包括每周与国务院成员一起访问白宫)。1943 年,斯科特被一名在「自由法国」工作的官员招募到刚果布拉柴维尔(当时是法国殖民地和抵抗运动中心),做无线电业务工作。
解放后,她先后为一位女国会议员和另一个政府部门工作,1945 年,她受聘并被派往欧洲,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新闻随员,后者当时正担任纽伦堡审判的美国首席检察官。同年回到纽约后,她在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担任首席编辑。
图比亚纳发现的重要证据表明,从1940年到1945年,斯科特很可能是苏联的间谍。她从未受到正式指控,但她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被揭示了出来。在1948年,她被联合国解雇,被剥夺护照,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骚扰。她短暂地在一家左翼新闻报纸工作,然后又在另一个工会工作过一段时间。
在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勉强维持生计,从事诸如临时保姆和打字员等低收入工作,她觉得生活毫无盼头。就像她写信给特吕弗时说的:「在我年轻时,我是一个『名人』,但后来,我陷入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并最终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把我抛在了后头,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被忽视。」

海伦·斯科特
然而,人生第二幕的帷幕已然拉开。1959年,斯科特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法国电影办公室」正在招募双语(法语和英语)秘书,这个政府机构旨在美国推广法国电影。她在那里成为了一名宣传人员,并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发泄她革命精神的出口。在她了解到新一代年轻法国新浪潮导演崛起的故事后,斯科特(当时只是一个偶尔看电影的人)使这一运动——以及这个词汇——在媒体上得到了显著的关注。
随后,新浪潮如闪电般来临。1960年1月,她被派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迎接当时年仅二十七岁的特吕弗——他来美国领取他的第一部长片《四百击》获得的纽约影评人协会奖。当他从护照检查处出现时,他们的目光相遇,对斯科特来说,这就是一见钟情。

《四百击》(1959)
斯科特看了《四百击》后,完全被这部电影迷住了,而特吕弗的出现完全改变了她的经历。他们很快成了朋友——柏拉图式的朋友,但这种看似一见如故的联系很快发展成为多方面的专业合作。特吕弗在纽约期间,他们建立了友谊,而斯科特在他离开后很快通过一批信件进一步加深了这份友谊。(当特吕弗的回信不够走心时,她会责备他。)特吕弗虽然刚开始有些拘谨,但后来还是向斯科特倾吐了自己的心声:他与玛德琳·莫根斯滕的婚姻以及他们的离婚;他与让娜·莫罗(他的第三部长片《祖与占》的女主角)以及和年仅十七岁的女演员玛丽-弗朗丝·皮西尔的婚外情;他抗议法国发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政治活动;以及他对自己事业的担忧。

特吕弗与让娜·莫罗
就在特吕弗决心创作他和希区柯克的访谈录(以反驳大多数美国影评人对希区柯克过低的评价)的前一年,斯科特也想创作一本特吕弗的灵感之书,收集他自己发表的访谈录,作为自画像式的作品。(他们最终没有实现这个计划。)斯科特的学习之路是如此幸运,在特吕弗的远程指导下,斯科特在纽约看了大量新浪潮电影,她仿佛在接受电影的洗礼。
当她看到戈达尔的第一部长片《精疲力尽》(1961 年初在美国上映)时,她立刻就被这部电影吸引了,并在纽约与戈达尔进行了一系列热情洋溢、相互欣赏的会面,她在写给特吕弗的信中说:「人们可能会钦佩他的才华;他有巧妙的创造力,但是如果他作为一个导演没有进步,他的作品就不会有太大的希望。」她发现特吕弗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他的电影也赞赏有加;她也认为应该承认:「过了一定的年龄,真爱就是两个人的幸福。除非像戈达尔认为的那样,爱等同于痛苦。」

《精疲力尽》(1960)
斯科特与瓦尔达和雅克·德米相处的很融洽,她对他们的电影赞不绝口。她也很欣赏阿伦·雷乃的作品,并与他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她同时批评了他和戈达尔:「戈达尔最大的弱点是蔑视观众,至于雷乃,他不理解观众,因为他个人离人类太远了。」希区柯克是她第二亲近的电影人,在采访(她是现场翻译)和多次会面(她是重要的介绍人)的过程中,希区柯克欣赏她的智慧和犀利、尖刻的幽默。
在一次谈话中,这位六十多岁的导演想知道为什么他在伦敦短暂停留期间没有收到她的消息,斯科特告诉特吕弗她是如何回答的,以及她心不在焉的原因:「我告诉他,鉴于他直到 25 岁才知道生活的真相(月经),我觉得他还太年轻,我无法向他解释女性的更年期意味着什么。」

海伦·斯科特与希区柯克
特吕弗开始着手写希区柯克的书,他告诉斯科特,这是为了纠正美国评论界的错误判断,而他的主要动机是向希区柯克学习。希区柯克向斯科特透露:「对我来说,我的面前是空荡荡的银幕和两千个空座。我必须填满它们。」作为制片人(拥有自己的制片公司)和导演、电影界的商人和艺术家,特吕弗将这个观念牢记在心。
他在美国评论家中的重要地位和在美国观众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科特与评论家、记者和发行商的合作。这种努力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新浪潮几乎成为了失败的代名词——阿涅斯·瓦尔达的《五至七时的克莱奥》,雅克·德米的《萝拉》和雅克·里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等电影在评论和票房上都遭遇了滑铁卢,这似乎暗示着一种颓败的趋势。
1962年,斯科特对特吕弗写道:「事实上,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人们惊奇地发现了法国新浪潮的壮举。当然,人们随意地使用这个术语,但在纽约,它已经变成了贬义词,令人惊讶的是,在《萝拉》的评论中,这个标签甚至成了一个侮辱性的词语。」

《萝拉》(1961)
1963 年创办的纽约电影节(斯科特也参与了电影节的推广工作)让六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新一代观众开始关注这一批导演的作品,这才将新浪潮确立为电影艺术的新标准。当时,特吕弗已是年轻的电影大师。(1965 年,斯科特在写给特吕弗的信中,以挽歌的口吻讲述了新浪潮的发展历程,他还强调了特吕弗在艺术上和个人性格上与戈达尔的差异,并建议他将这些差异公之于众——这是特吕弗 1973 年与戈达尔在情感上激烈决裂的先兆。)
如果说特吕弗的艺术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成熟,并且在六十年代后期迅速向更深层次的艺术性迈进(如《骗婚记》和《野孩子》等影片),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与斯科特的友谊。

《骗婚记》(1969)
整个六十年代初,斯科特在给特吕弗的信中都充满了挑逗和挑衅,她从不掩饰对特吕弗的强烈依恋,同时对这种感情进行深入细致的心理分析:「你的信点燃了我们的爱情,或者至少是我单方面的感情。出于对玛德琳的礼貌,人们或许会贬低我对你的痴迷,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玛德琳断言你太难以抗拒,无法激发柏拉图式的爱情,她似乎总是对这个问题心存疑虑,而我则更乐意接受她的俏皮话,因为我对她的俏皮话受宠若惊。」
这段复杂关系所蕴含的丰富文学性成为了特吕弗性格的一部分,这段友谊丰富了特吕弗的艺术,也赋予了斯科特新的生命。1966 年,斯科特开始了更充实的生活,与特吕弗一起在英国拍摄电影《华氏451度》,并搬到巴黎,开始利用他(和玛德琳)以及她在电影界的广泛关系。

《华氏451度》(1966)
她成了这个世界的支柱,出现在电影节和各种聚会上,是字幕员、中间人、顾问、名人、朋友、受欢迎的客人,甚至以一种反常的方式,成了某种象征——法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和辉煌崛起的生动象征。1968 年,在沃伦·比蒂为《雌雄大盗》做宣传时,她陪伴沃伦·比蒂度过了一段有趣的冒险之旅。

《雌雄大盗》(1969)
她曾在戈达尔 1967 年的影片《我略知她一二》以及特吕弗的《婚姻生活》和《最后一班地铁》有过短暂的出场。她和米洛斯·福尔曼、罗曼·波兰斯基、克洛德·勒卢什和克洛德·贝里都合作过。她与罗伯特·本顿(《雌雄大盗》的联合编剧,这部电影一开始是给特吕弗写的)一直保持着友谊。
1980 年左右,比尔·默瑞在巴黎为动画片《缺失的环节》录制配音时,本顿为她牵线搭桥,她和比尔·默瑞成为了生死挚交。图比亚纳在书中引用了《纽约客》记者莎拉·拉森在纽约影评人协会晚宴上的报导,比尔·默瑞提到斯科特时说:「她真的会骂人。她真的、真的会骂人。」
尽管斯科特在巴黎从事着各种电影活动,但她的生活并不富裕。1981 年,特吕弗从她那里买下了她寄给他的信件,希望将他们之间的通信出版,以在经济上给她提供帮助。1984 年,特吕弗死于脑瘤。特吕弗去世后,图比亚纳采访了斯科特,并鼓励她撰写回忆录,但她一直没有动笔。她于1987年去世,享年72岁;这些信件就是她的回忆录。她与特吕弗的书信往来是这段暗中影响着电影世界的友谊的文学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