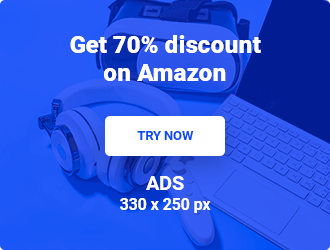尊敬这个导演,主要是因为他被迫害?
作者:乔纳森·罗森鲍姆
译者:易二三
校对:鸢尾花
来源:New Lines
(2023年6月28日)
贾法·帕纳西是伊朗仍在世的最重要的电影导演,在我看来(至少在我所熟悉的电影导演中),西方观众对他的尊敬似乎更多是因为他受到的迫害,而不是他的作品,这既令人遗憾,又自相矛盾。
他的首部长片《白气球》(1995)是第一部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重要奖项(金摄影机奖)的伊朗电影,而且之后的四部长片《谁能带我回家》(1997)、《生命的圆圈》(2000)、《深红的金子》(2003)和《越位》(2006)都在西方的各大电影节上有所斩获。

《白气球》
但直到帕纳西于2010年被捕,被判处六年监禁,并被禁止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从事任何电影制作活动,他才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他被指控犯有「反体制宣传罪」,因为他参加了2009年绿色运动抗议活动中一名遇害学生的葬礼,并试图拍摄一部同情这次活动的电影。)
此后,帕纳西不顾禁令,奇迹般地又拍摄了五部电影,并在每部影片中都亲自上阵。尽管这些影片在资源和拍摄条件上都受到严重限制,但却比他被捕前于1995年至2006年期间拍摄的五部影片更受关注——早前的这五部电影都由国家出资制作,但其中几部在伊朗当地影院都曾被禁。

贾法·帕纳西
帕纳西被捕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这不是一部电影》(2011)完全是在他被软禁时在自家客厅里拍摄的。而帕纳西最近的作品《无熊之境》(2022)则在伊朗和土耳其边境附近拍摄,故事情节复杂得多,获得了去年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特别奖。
遗憾的是,与帕纳西于2010 年之前拍摄的那些成就更高、更细致入微的影片相比,公众对这些逃亡式的作品要熟悉得多。值得补充的是,《生命的圆圈》和《越位》都对伊朗妇女的境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白气球》和《深红的金子》则对阶级关系及阶级差距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无熊之境》
帕纳西迄今为止拍摄的10部电影都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美学特征:一是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帕纳西的主要导师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中常见的纪录片式手法为基础;二是将电影本身视为每部影片主题的一部分,具有自我反思和现代主义的视角——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追溯到基亚罗斯塔米,而且经常给人一种影片是实时发生的印象。
这一点在《越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该片大部分镜头都是在2005年6月8日伊朗队与巴林队进行世界杯预选赛时,在德黑兰的阿扎迪体育场内外拍摄的。

《越位》
需要补充的是,基亚罗斯塔米在开始自己的电影生涯时,曾为国营的儿童与青少年智力开发中心(又简称「卡努恩」[Kanoon])创立了一个电影部门,这使他摆脱了通常的商业限制,但也使他的早期电影带有某种教育性质。
帕纳西继承了这位前辈的一些说教或教育基调,以及后者的现代主义风格——正如《谁能带我回家》中所呈现的那样,该片徘徊于一个小女孩与女演员的虚实冒险之间,前者试图独自找到从小学回家的路——后者恰恰是为了讲述这则故事而扮演小女孩,并且最终想要罢演回家。

《谁能带我回家》
更具有教育意义和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可能是《生命的圆圈》,在许多方面,它都是帕纳西最伟大、最大胆的影片(也是他在伊朗被禁的影片之一),它讲述了从一个女婴在医院出生到一个中年女人被关进监狱等多位女性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是对伊朗社会中女性遭受的残酷待遇的持续且愤怒的呐喊。
换句话说,这是一次从一个监牢到另一个桎梏的循环之旅。最重要的是,《生命的圆圈》预示并阐明了二十多年后震撼整个国家的以「妇女、生命、自由」为口号的运动的许多方面。影片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在环形地点的环形镜头运动中展开的。
在《白气球》和《越位》中,前者讲述了一个小女孩(由阿怡迪·莫哈曼德哈尼扮演,她是《谁能带我回家》的女主演米娜·穆罕默德·汉妮的妹妹)为了在伊朗新年买到一条幸运金鱼而付出的努力;后者讲述了德黑兰的女孩们为了能在阿扎迪体育场观看一场足球比赛而伪装成男孩,却因此被抓。(在伊斯兰共和国,女性被禁止出席观看男性的体育比赛。)

可以肯定的是,这两部喜剧都有其启发性,甚至是说教性的一面。在《白气球》的结尾,中产阶级女主角不假思索地冷落了帮助她的工人阶级男孩。
和《生命的圆圈》一样,《越位》的结尾也是在一辆载着被捕女性的警车里,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那些不得不逮捕这些女孩的看守——这两个群体都被视为严苛法律的受害者。
帕纳西是一位信奉机会均等的讽刺作家,他的大部分喜剧都是在这种前提下创作的,因此他可以在这两个群体之间自由穿梭,而不失去讽刺的重点。事实上,影片的最后,女孩们和士兵们都带着烟花离开了押送车,加入到狂欢的人群中,高唱伊朗国歌,庆祝国家足球队的胜利。
在2016年一部名为《此刻你站在哪里,帕纳西?》的纪录短片中,帕纳西开车送一位同事去德黑兰郊区的阿巴斯的墓地,同时讲述他被捕前的所有电影都是如何描述他在街头亲眼所见的伊朗社会,而他被捕后的所有电影都只能描述远离社会的他自己的境况。
简而言之,这解释了为什么他早期被忽视的电影比他最近的电影更有持久的价值,尽管后者也证明了帕纳西的坚韧不屈和聪明才智。

《此刻你站在哪里,帕纳西?》
要欣赏帕纳西的早期作品,就需要了解非西方社会,在那里,女性可以吸烟的意义与西方不同;女性的着装要求由当局强制执行——有时甚至是粗暴地强制执行;关于结婚和离婚的法律对女性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忽略这些问题可能会让人更容易将帕纳希视为一位殉道者,而不是一位社会分析家或批评家。
《深红的金子》讲述了一个令人震撼且魂牵梦萦的传奇故事:一名曾参与两伊战争(1980-1988年)的披萨外卖员试图抢劫一家珠宝店,最后开枪打死了店主,并吞枪自杀。该片的灵感来自阿巴斯发现的一则报纸故事——他也是该片的编剧。
影片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的差异和受伤退伍军人的怨恨——这比《生活的圆圈》和《越位》中所涉及的问题更接近我们西方人自己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连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差异都不了解,那么我们对帕纳西更感兴趣的可能是他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而不是他那些充满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深红的金子》
贾法·帕纳西是谁?1960 年,他出生在伊朗米亚内镇的一个阿塞拜疆工人家庭,家中有四个姐妹和两个兄弟。他曾在两伊战争中担任过两年的军队摄影师,随后在阿巴斯的电影《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中担任副导演,在此期间,他拍摄了多部短片和纪录片。
西方人对伊朗的无知简直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将伊朗视为一个简单的整体,而事实上,伊朗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虽然波斯人占多数,但大约40%的伊朗人属于其他民族——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卢尔人和土库曼人。帕纳西从小在自己家里讲阿塞拜疆语,与其他伊朗人则讲波斯语。(《无熊之境》全片用的都是波斯语和阿塞拜疆语。)

我们还必须问的是:帕纳西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胆略如何?2023年2月,是什么样的动荡局势最终迫使他在狱中绝食?为什么两天后政府决定让他回家?我与帕纳希的短暂接触、我对伊朗的两次访问以及我所了解到的伊朗电影制作环境和审查制度,大致提供了一些关于伊朗2023年2月之前几年的见解。
例如,帕纳西在第一次被捕后,要求狱卒不要因为他电影导演的名人身份而给予他任何特殊待遇,这可以算是他的胆略。事实上,成为一名电影导演是当今伊朗工人阶级唯一可以实现阶级攀升的方法之一。(这个事实甚至也是阿巴斯开创性的早期长片《特写》的关注重点,该片遵循、重述甚至延伸了侯赛因·萨布齐安的真实故事——侯赛因是一个贫穷的伊朗电影爱好者,为了获得德黑兰一个富有的土耳其家庭的认可,他假冒真实生活中存在的电影导演 穆赫辛·马克马尔巴夫,声称他想与他们一起拍摄一部关于他们的电影,直到他被捕。在影片最后的情节中,阿巴斯安排了一次马克马尔巴夫和重获自由的侯赛因的会面,然后让他们两人一同去拜访那个土耳其人的家。)同样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深红的金子》结尾处毁灭性的暴力事件。

《深红的金子》
多伦多电影节放映《生命的圆圈》时,我通过翻译的帮助简短地采访了帕纳西,我惊讶地发现他坚称这部电影不带政治色彩——我觉得这无异于说猪肉是一种蔬菜。但在另一次关于这部影片的采访中,他更准确地解释了自己这么说的理由:
「一位政治电影导演往往致力于某种意识形态,试图通过作品来宣传这种意识形态,并攻击敌对的意识形态。在《生命的圆圈》中,我没有攻击或支持任何人。我没有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试图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每个人,用一面镜子来反映社会现实。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不同的政治角度来解读这些现实。我拍摄的是一部带有抗议信息的艺术电影,而不是一部颠覆性的政治电影。」

《生命的圆圈》
对于我们这些北美人来说,这其中的区别可能听起来很玄乎,但如果考虑到我2018年在德黑兰遇到的另一位伊朗电影导演的最新事例,大概就会明白这件事是很合乎逻辑的。那位导演每天都在拜访伊朗的审查人员,试图说服他们,在他的最新作品中出席女主角抽烟的镜头,并不具有政治颠覆性。
甚至早在2001年,当帕纳希从香港的一个电影节飞往南美的其他电影节,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转机时,他就对每次通过美国海关时都要被当作罪犯而接受指纹采集感到非常厌恶,因此他当时拒绝了再次经历这一程序。
结果呢?他被铐在长椅上长达十几个小时,房间里挤满了 「非法移民」,不被允许给任何人打电话,即使他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和行程的证据,还是被手脚捆绑着遣返回了香港。
纵然《生命的圆圈》在前一年勇夺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作为伊朗人的他可以在香港偷偷带着手榴弹安全通过金属探测器。甚至可以说,美国海关官员无理的排外行为最终迫使这部作品违背他的本意,而染上了政治色彩。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9年后,帕纳西在自己的国家也被当作罪犯对待,而此时距离他拍摄《越位》已经过去了3年——这是帕纳西最轻松的喜剧片,也是他最通俗易懂、最具娱乐性的电影。
但是,将美国海关和伊朗审查人员对帕纳西的不宽容并置,表明这两个多元文化国家之间存在着我们不愿看到或承认的相似之处。
尽管伊斯兰共和国法律严苛,镇压手段令人窒息,但伊朗仍然贡献了堪称世界上最具人文精神的电影。
帕纳西以他作为一个反叛者的勇气,以及拍摄伟大电影的才华和想象力,可以说是伊朗最伟大、最具典范意义的电影人之一,当然,他不仅是伊朗、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电影导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