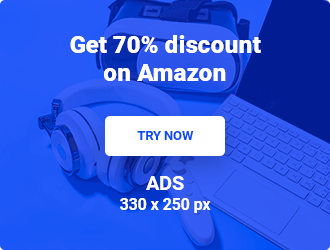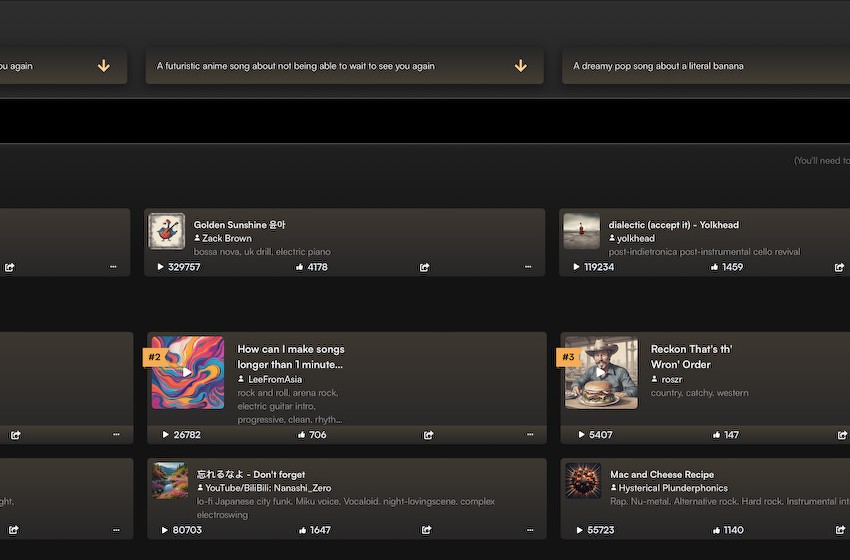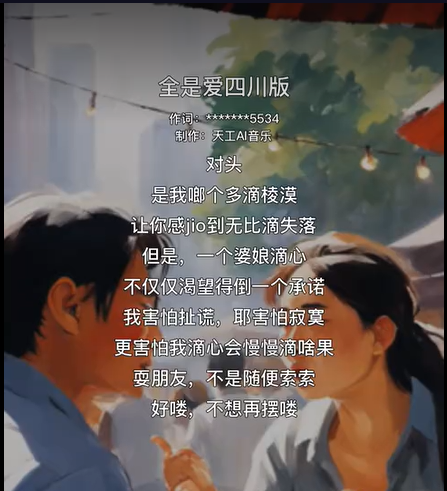请用身体作为思考的方式,回答“我是谁”






记者手记
一票难求,是我对电影《野蛮人入侵》的最初印象。
2021年6月,电影《野蛮人入侵》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拿下金爵奖评委会大奖,同年9月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映。而在北影节开票时,该片引众多影迷抢票,瞬间秒光。此后,我一直在影迷群中求票,仍然无果。
直至今年8月10日,《野蛮人入侵》终于被引进中国影院正式公映。前不久,看到这部影片后,我认为它真的值得当时的“一票难求”。
《野蛮人入侵》是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作品,讲述的是演员李圆满隐退离异后,成为了全职母亲,她一边照看难以管教的孩子,一边准备主演合作多次的导演的新片,这次新片的拍摄要求是李圆满要在武馆习武,学习武术动作,完成动作片的拍摄。然而在习武的过程中,状况百出,从母亲的身份再到演员、角色等身份中,李圆满一次次面对着“我是谁”的问题,探寻自我的冒险旅程就此开始……
“电影就是一切,一切都是电影”,我认为这句台词几乎完美概括了电影与生活的模糊界限,正如许多观众在看完《野蛮人入侵》后,一直在分析影片中的虚实叙事的结构。
8月3日上午,我见到了陈翠梅导演,当时她正在房间里接受另一人的视频采访,我听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导演平时都会看什么样的电影。陈翠梅回答说其实平时看电影比较少,更喜欢看书,读文学作品,但不论是电影还是文学,都是认识生活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生活,对自己有益处。
这一回答,让我想到了影评人“赛人”对《野蛮人入侵》的评论:“电影就是一切,远不及一切都是电影来得更加辽阔、深远,更能让我们对人,对人所处的时空葆有持久的注视。”
每个孩子的诞生就是一次野蛮人对文明社会的入侵
北青报:在观影前,我看了您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的采访,几乎都在谈论您成为母亲后,孩子作为“野蛮人”给您带来的种种体会。因此,我在看到电影的第一部分时,一直认为这是一部讨论孩子与母亲关系的影片。但越看下去我才发现,您想讨论的不只是这些话题。
陈翠梅:很多人都把这部电影定义为女性电影,可能现在很多观众正在渴望着一部女性电影的出现。而正如你所说的,电影开始的第一部分中,女主角的确面临着女性困境:她是明星,又是一位母亲,要一边演戏一边照顾孩子。但是到了后面,她开始慢慢去寻找其他东西的时候,作为女人的身份不再那么重要了。
电影中一直在重复问着“我是谁”的问题。最开始回答这一问题时,答案可以是名字、职业,我是谁的妈妈或是谁的妻子,而之后当这个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时,它就不只是属于女性的问题了,它是面向每一个人的问题。
北青报:在筹备这部电影时,您最初是想要讨论有关孩子和母亲的这个话题吗?
陈翠梅:2019年,香港天画画天影业有一个电影项目,他们把主题定为“爱情征服一切”,这也是我的第一部电影长片的名字。那时,我并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想好了我的电影片名——《我只要你爱我》,引用的是德国著名导演法斯宾德的电影片名(中国翻译为《我只希望你们爱我》)。我大概的想法是拍一个科幻小品,故事是关于一个女孩子去和人工智能聊天,谈论自己喜欢的书和音乐,与人工智能谈恋爱。
后来,朋友开玩笑说可以拍一个动作片的时候,我又改成了完全不同的故事,类似于中国之前上映的由唐晓白执导、谭卓主演的电影《出拳吧,妈妈》。我改成了一位中国独立导演找了一位女演员,要她演一部关于MMA(综合格斗)的电影,送她去泰国普吉岛的MMA一条街去学习,但是过了三个月,导演跟她说有其他的演员带资进组,不需要她出演了。于是,女主角真的跑去参加了MMA的比赛,并且赢得了冠军。
这两个构思都是关于为爱所做出的努力。第一个故事是希望人工智能来爱她,第二个故事则是希望观众来爱她。后来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几个人真的去了普吉岛MMA一条街,同时我还带着我的孩子去了,结果因为我的小孩很能搞怪,我被搞得很狼狈,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计划统统被他打乱了。
当时,我想到了曾经听过的一句话,“每个孩子的诞生,就是一次野蛮人对文明社会的入侵”。在那时我才对这句话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所以,我当时想,应该把女演员写成一位妈妈,她要带着孩子去做MMA训练,同时我也把电影片名改为《野蛮人入侵》。
接着我把剧情又修改成了小孩突然被泰国黑帮绑架了,女主角则变成了“野蛮人”的身份,用刚学的MMA去打斗。这些设计都是在后来慢慢想到的,最开始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类型片而已。
我们常常忽略身体的直接反应引发的思考
北青报:您在拍摄的过程中,会像电影中的角色一样被孩子不断地打扰吗?
陈翠梅:没有。我在拍摄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到妈妈那里了。我们总共拍摄了一个月就杀青了,拍摄过程比较快。原本我们要在2020年4月开拍,但是因为马来西亚的疫情,那年3月18日就突然开始封锁管控。原本说是封锁两星期就好,刚好可以到4月开拍,但实际上一直延到6月才开始拍摄。
原计划是分学武前和学武后两部分拍摄,结果我们就在6月拍摄了学武前的剧情,又因为吉隆坡的管控政策,我们不能去计划拍摄的一个东海岸小镇,只能在吉隆坡拍摄。于是在吉隆坡拍摄了三天的内景,等到8月我们才又去东海岸小镇拍摄了外景。
北青报:这次您亲自上阵饰演女主角,完成了所有的打戏。那么您在开拍前,做了多久的习武的训练?
陈翠梅:其实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三个月的MMA。那时候是每天学泰拳。到了2018年,我想要尝试重新学MMA的时候,却发现我的整个身体因为生小孩,大伤元气,没有办法再去做很多的事情。不过,2019年到2020年要拍戏的时候,我又去学了巴西柔术。
北青报:习武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体会呢?
陈翠梅:我不知道我的体会是一开始就产生的,还是后来感知到的。经过习武,我发现我们通常认为的“思考”,是“有语言的思考”。或者说,我们只把那部分关于理性的、逻辑的思考称之为思考,而那些不理性的事物却不被称为思考。比如我们在捏陶瓷的时候,要捏出一个形状,是需要手去运用很多触觉的,有轻重缓急的分寸,那么我们的手就是有思考的——我们的身体本身有着思考,却总是被我们忽视,因为它没有语言。
北青报:就像电影中所展现的,当我们被打的时候,身体本能地去躲避和反抗。
陈翠梅:对,身体的反应是最基本的“自己”。当我们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时,总是会给自己编故事,用理性、合理的方式讲出自己是谁。但是回归到身体层面,其实所谓的自己就是不想死的自己,这是最原始的答案。我们以疼痛感知到自己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逻辑和理性,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想死,不想痛,想要避开危险,这都是用整个身体来做反应的。
我们总是没有考虑到其他的感知也是思考的一部分,比如我为什么会生气、为什么会高兴或是通过悲伤来反映某件事,其实这都是跟世界产生连接的一种方式,但我们常常会倾向于“理性思考是高级的,是文明的;而身体感官产生的思考则是野蛮的,不文明的”。
北青报:所以在电影中,从武馆出来后,女主角遇到的老和尚,代表的是野蛮与文明的思考上的不同吗?
陈翠梅:不是的。老和尚是武馆师傅的一种延伸,他们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东方和西方对于武术的概念是不同的。西方会认为武术就是动作片,而东方拍摄武术就会涉及到哲学,比如一些禅宗上的思考。那么老和尚的形象是类似于达摩的形象,他的思路是很跳脱的,也会演变成许多文字。有些禅宗师傅是会“当头棒喝”的,比如电影中的武馆师傅就会突然打我一拳,让我来不及反应,但是一拳打下来就会突然明白一些哲思,这是无法言说的。
我没有要拍出好电影的野心拍电影只是为了我自己
北青报:当您拍摄打戏的时候,身体的疼痛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受伤也是常事吗?
陈翠梅:在拍戏时,我受过一次伤。在彩排的时候,剧情是被武馆师傅踢了一脚退到墙上,结果因为我退得太快,坐在了地上,当时我觉得没事,只是忍着痛继续排练,结果过了很多天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脊椎有些错位,这一次比较重,其他时候还好。
北青报:对您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挑战,为什么不用专业演员作为主角呢?
陈翠梅:两个因素吧,一是像杨雁雁和李心洁这样的影后,确实很会拍打戏,但是邀请她们演出的费用会很贵,她们也不可能跟组训练三个月。二是出于我的私心。如果请了顶级的演员,这当然会对电影票房有好处,也会让我更专心地执导影片,但如果我亲自上阵去体验的话,尽管我对票房没有号召力,可是我能够肯定的是,这样的方式会“对我好”。
我没有要拍出好电影的野心,拍电影只是为了我自己,因此我会选择“对我好”这个选项。本身拍摄这部电影,我就是想思考清楚“什么是自己”或者说“我是谁”的问题,经过这次的体验和经历,会让我通过自己的身体,产生一次深刻的思考,于我而言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为什么要创作?为什么要做艺术?说到底还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要自己去演这部电影。如果我们做了那么多,却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是要干吗呢?其实到最后,你所体验的所有东西,都是要拿来用的,电影也是一样。我们不应该只是把电影拍好或是热爱电影,以为那就是一切了,其实应该通过电影让我们更了解其他人,更有同理心,更能理解这个世界,更让我们可以体会到生活才更重要。
北青报:在电影中很多影迷梗,其中有一句玩笑的台词是“你不会是找我来拍洪尚秀电影吧?”其实在我看完电影之后,我认为您的这部电影在形式上还挺有“洪尚秀”式的设计。
陈翠梅:我很喜欢韩国导演洪尚秀的电影。我最早是在2006年看到他的《女人是男人的未来》这部影片,就又去找他以前的作品来看。我非常喜欢他的《生活的发现》《江原道之力》,后面他拍了《夏夏夏》,洪尚秀似乎有一份要跟黑暗告别的宣言——电影中他的朋友就留在了黑暗的地方,而他去向了光明的地方。在这一部电影之后,我真的觉得洪尚秀变了,他变得很光明,他终于找到了他要的东西,不知道这是不是跟他谈恋爱有关系。
我最早学到他的剧作形式是“重复”。在《生活的发现》中,后面和前面有很多重复的部分,比如这句“修成人不容易,你不要再做禽兽了”台词被重复了三次。电影《这时对,那时错》则是整体内容的重复。
我发现完整叙事中的因果关系是假的
北青报:电影中很多的情节是否真的来源于您的生活?我记得有一句台词是:“当你成为了母亲,你的身体就是属于社会的。”作为一个男性,我感到惭愧的是很难真正理解这句话。
陈翠梅:正在怀孕的时候,我真的在电梯里遇到过陌生人来摸我的肚子,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因为总会有人很关心孕妇,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来问一问,几个月了?什么时候出生?然后就会来摸一摸我的肚子,尽管他们并不会让我感觉到可怕。
所以,我会觉得因为变成一个妈妈,很多东西就改变了,包括这种奇怪的社交距离。可能是因为大家在原始心理上,还是会对小动物和小孩子有一种直觉的呵护吧。
而等到小孩正在成长的时候,情况又变了——所有人都会跑来跟我说,“你怎么可以让他这样”“你怎么不抱住他”等等的话,好像每个人都开始来管我。在此之前,我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有了小孩之后,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有权利来教父母怎么做,或者说这个小孩是属于社会的,我们作为父母只是为这个社会来照顾小孩而已。
北青报:很多观众会在网上讨论这部电影的虚实结合的部分,会分析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一部分是戏中戏的结构。而我在看完这部电影后,会把这部电影当作全部是虚构的,自片头的“开拍”那一刻起,摄影机就开始构建着一部电影了。
陈翠梅:我从来没想过这是一部“元电影”的影片,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电影讨论的是从“不知道自己是谁,完全没有自主的控制”,到之后“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至少是可以对自己的身体运用自如”,再到“失去记忆之后,走向更深的一个探索之旅”。在这整个旅程中,我设计的是全部都是假的,是电影式的。电影中并没有“戏中戏”的逻辑,它是没有边界的。尽管电影开始的第一部分看起来很像真实生活,但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我还怕这一设定不够明显,所以在片头一开始又加了一句“开拍”的背景音。
北青报:电影的后半段问了一个《黑客帝国》里的经典问题“你选择蓝色药丸还是红色药丸”,引得观众大笑,这是一个非常存在主义式的问题,所以这是您一直面对的问题吗?
陈翠梅:其实还是要回到刚刚谈到的理性思考的问题上。理性思考会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谁?我们今天在这里对谈是因为什么……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生活的,我们会给自己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然而完整的故事一定有因有果,如果今天是果,那么以前便是因。但我越来越发现,这一叙事上的因果关系是假的。因为我们总是在今天得到的结果中,回溯以前的事情,在其中找到合理的原因,再倒推出合理的因果逻辑,这是我们自己塑造的因果关系,这是不真实的。当我们一次次追问“自己是谁”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构建出来的,是自己去想象和合理化的。我们努力寻找出一个理由,将其编成故事,这仍然是假的。
因此,我认为回答“我是谁”的一个方法,是要用心和身体直接来解释自己是谁,这并非存在主义,而是在讨论:是不是可以用“语言思考”之外的方式,去谈我们到底是谁?
文/本报记者韩世容
供图/大象点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