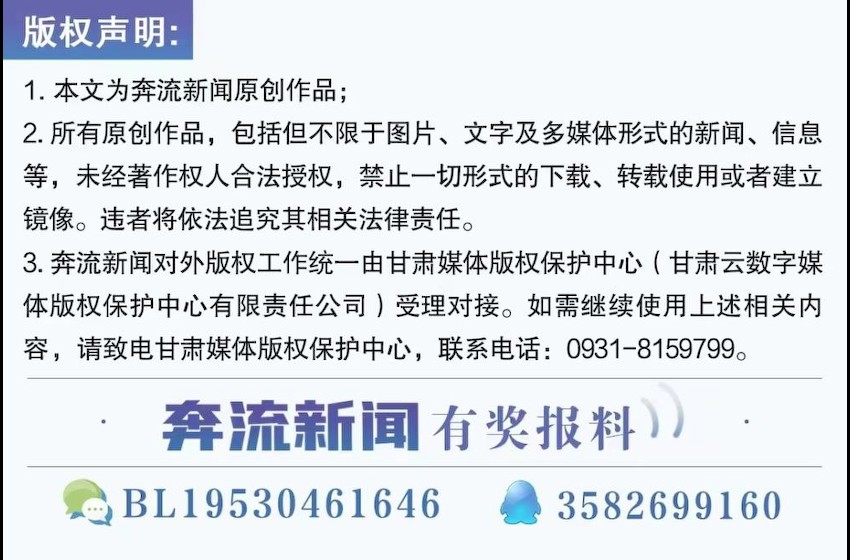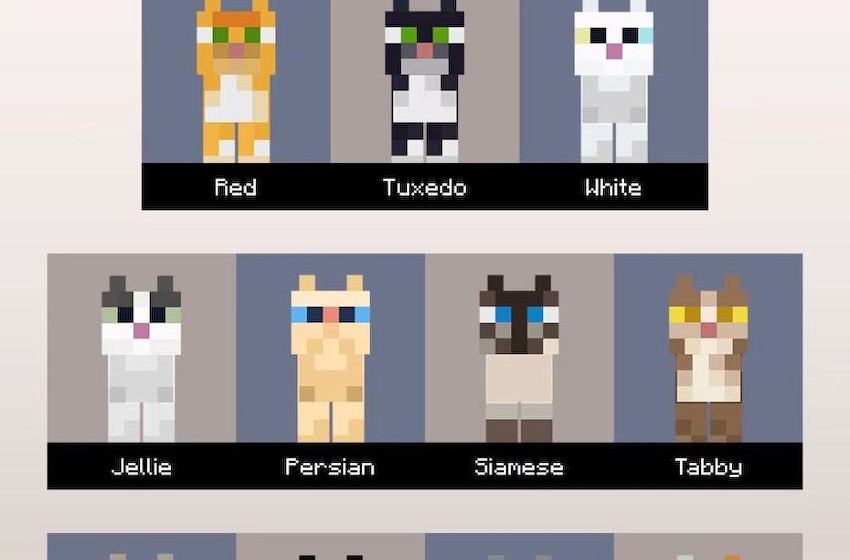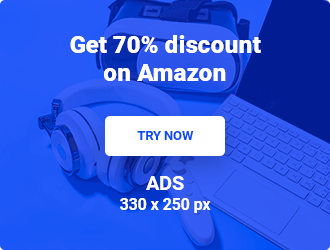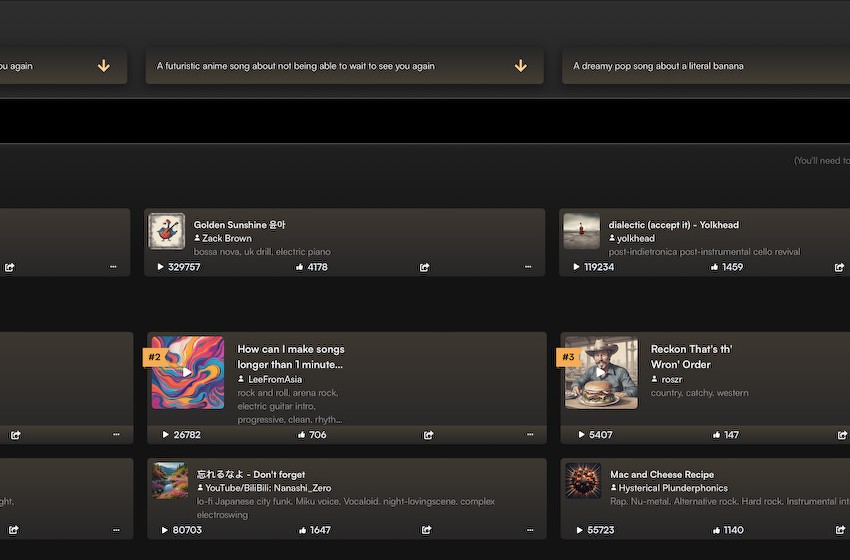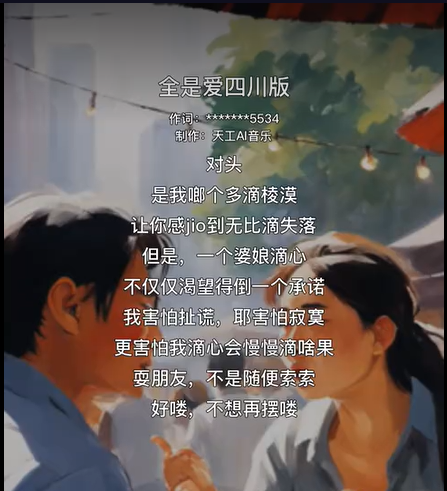《野蛮人入侵》导演陈翠梅:我可能在哪里都是个另类
8月10日,马来西亚电影《野蛮人入侵》在中国大陆上映。早在2021年,本片就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当时已有不少观众称赞该片形式上的创新。影片融合动作、女性、迷影等丰富元素,引起了小众影迷解读的狂欢。陈翠梅这一名字,慢慢开始在影迷圈传开了。

然而,陈翠梅在收获赞誉之余,也引起了争议。近期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现在“女性导演享受到了非常多红利”“男性导演反而少了机会”的言论,让部分国内观众感到不适,他们批评导演误判了当前电影行业的现状。陈翠梅在随后的道歉回应中称“当时的表达由于脱离了一定的语境,表达也不够完整,看起来的确引人误解。”国内不少业内人士出来为她辩护,但依然有部分观众表示不能认同。
南都记者在采访陈翠梅的过程中留意到,她是个经常自我怀疑的人,有点不善言辞的她,言语中常用“可能”来让事情不那么绝对化和留有余地。她的坦诚时常让她暴露自己的局限,同时她的开放,也让她愿意去听取和吸收反对者的批评。在她近期的豆瓣动态中,我们看到她在跟善意的中国观众虚心请教。比起部分批评者剑拔弩张的训话,陈翠梅的谦和显得优雅和可爱。对一个创作者而言,比起表达某种“正确”的主义,真诚也许才是他们更重要的品质。

导演陈翠梅
1
“我其实是个‘矛盾体’”
南都娱乐:有人评价《野蛮人入侵》是东亚版的《芭比》,你对这个称号是否认同?
陈翠梅: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的电影会被叫东亚版的《芭比》,可能是因为上映时间一前一后,并且导演都是女性。我觉得好像很难拿来比较,我的电影反而可能跟《瞬息全宇宙》形式上有点像,它用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手法,把一个家庭里面分裂的情感当作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事情来拯救。
南都娱乐:你说过《野蛮人入侵》是部很私人化的作品,是部“私电影”,目前很多中国观众用了不少概念术语去解读,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被概念化?
陈翠梅:我讲“私电影”时不代表我讲述的都是我的个人事迹,可能因为我自导自演,导致观众误以为主人公李圆满就是我。的确,我在表演中有一些自己生活的小细节,但是大部分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很多已经成为母亲的演员朋友,从她们的一些生活状态,还有事业上的转变来取材。“私电影”是我拿来思考的一个工具,它不是为了达到商业目的,有点像写散文,用一篇比较思辨性的文章来讨论一件事情。我没有想要拍自传性的作品。
我构思这部电影先是以一个玩笑为契机,它先是一个玩笑,然后再是一个类型片。这部电影的主题可能是写到第三、四稿才出现的。我一开始根本不是想讲关于“寻找自我”的主题,是到了后面才慢慢落实。毕竟创作时还是在很平实地生活,所以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一些新的思考就会带入电影创作里面。我从2019年7月开始写剧本,有一个故事大纲,到2020年1月的时候,已经大概成型,后面只是改动了一些细节,大概花了6个月。

南都娱乐:中国观众特别关注你在电影中女性主义的表达,也期待你对女性议题发声,中国观众的这些反应跟马来西亚观众是否相似?不相似的话,有没感到错位感?
陈翠梅:在马来西亚其实很少有女性主义的讨论,我们那边讨论的一般是阶级问题或者是种族问题。中国可能是这几年女性议题特别热,大家好像特别渴望看到比较强大的女性导演和女性电影。
马来西亚观众的关注点可能在电影中演前夫的男主角阿南,他本身是一个在印尼跟马来西亚都非常有名的男明星。观众也会关注我的打斗戏,大家会比较惊讶于我突然拍了部打戏,他们在电影的类型讨论较多。
大家渴望某一种女性导演的形象,当这个形象不符合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失望和错位吧。但我自己倒不会有错位,我反正一直就是这样的,纯粹地拍自己想要拍的东西,这个可能跟我的整个文化背景和成长经验有关系。我也不是典型的马来西亚华人,在大家的眼里我老是“吓人一跳”,不太循规蹈矩。我鼓励他/她们的激进表达,但我不希望他/她们去限制别人。导演本身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这个因素不可控。
南都娱乐:目前电影行业女导演还是偏少,你在近日回应争议的说明中提到对“女导演”这一身份感到怀疑,更希望自己作为导演被认可,你这种试图“去性别化”的心理是怎么来的,能否再展开说说?
陈翠梅:可能是早期我开始拍短片的时候,有人会说我的电影是女性主义电影,我挺疑惑的。后来我拍了部没有女性,只有四个男人主演的短片叫《蘑菇兄弟们》,观众却说这是部特别女权主义的短片。后来时间长了,我就接受了别人对我的各种评价。
我觉得很多女导演不太有自信,或者是觉得外界对她们不公平,大家应该要多鼓励她们拍更多元化的电影,无论是商业片、类型片、文艺片等等。女导演可以不用针对自己的性别限定题材。

南都娱乐:在工作中有没有哪一刻,让你切身地体会到男女导演的差异?
陈翠梅:一直都有。我觉得女性导演可能更容易理解他人,更容易共情,甚至更愿意付出。但这些特质有时候并不是好事,很多很聪明的女孩子已经非常有才华了,早已具备当导演的能力,但是她们不太愿意站在前面,反而比较愿意服务于他人。我觉得应该鼓励更多的女导演出来拍,而不是去对抗什么。
我自己是个“矛盾体”,也经常自我怀疑。有时候我看到某些男导演,他们的剧本也不一定比我好,但是比我更有自信,我也很诧异。我们似乎太过认定导演是很强势的、有领导力的人。很多人看到我时会觉得,陈翠梅怎么一点都不强悍,没有一个导演的样子。很多人想象导演的样子就是很男性化的、很强势的人,一站出来就特别有气场,他的话可以震住全部人。我可能比较傻,常常乐呵呵的,会一直笑,看起来不是大家想象的导演形象。有时候,我会鼓励年轻导演不一定要假装很强悍,不需要去表演成一个导演的样子。哪怕你本来就比较害羞的,那也没关系。我们要打破大家对导演刻板的期望和想象。

南都娱乐:可以推荐一些影响过你的马来西亚女导演吗?
陈翠梅:马来西亚比较重要的导演都是女导演,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们的确没有对女导演不公的现象。我刚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马来西亚最有名的女导演叫雅丝敏·阿莫( Yasmin Ahmad),名字的意思是茉莉花,她已经过世了。雅丝敏·阿莫拍了特别多社会议题的电影,尤其是关于种族之间的不公平。她的电影里,有五六部可能都在谈论异族恋,就是华人跟马来人之间的误会。她本身是一个很独特的人,说话特别多争议,但是人又特别可爱。她心有大爱,她其实有点像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电影里面的人。她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穆斯林马来人女导演,她虽然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她说话特别大胆,特别搞笑。我的第一部重要短片叫《丹绒马林有棵树》就是找了她赞助,她是我的一个恩人。雅丝敏不单只是对当时马来西亚导演具有启发性,(后来)有很多导演模仿她的东西,她的作品常常表达:虽然马来西亚有各种种族之间的不和谐,但是可以用爱来解决。
我们那边有名的女导演还有好几个,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最有名是雅丝敏,然后另外一个拍商业和爱国电影很成功的女导演,她叫舒米·巴巴。她也是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新浪潮时期的导演,在马来西亚电影历史上非常重要。马来西亚女电影人的地位好像确实比较高。
前一阵子那篇不断被引用的采访,谈论的内容是有特殊的情境,是在国际电影节的语境,尤其是欧洲电影节。电影节是一个很理想化的地方,他们会放大少数人的声音。这个圈子游离于真实世界之外,比较“真空”。现实中不是那样的,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不单只是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我自己也经受过种族的不平等。

2
主角名源自香港武侠剧
南都娱乐:我留意到主人公经常以东南亚来指代自己生活的地域,而不是只说马来西亚,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你电影中的一个设定,还是说背后代表了马来西亚人的普遍观念?
陈翠梅:东南亚以前其实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国界,它就是马来群岛。这些马来群岛的人,可能来自婆罗洲,可能来自爪哇岛,可能来自苏门答腊岛,然后来到马来半岛。人们可以很自由移动,国界没有那么清楚。一直到了欧洲人来殖民之后,才清楚地划分界限。在此之前,人们的流动性很大。现在电影业也开始有很多东南亚合拍片,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故事放在整个东南亚。比如我的这部电影就是菲律宾制片,泰国制作后期等等。现实中我们大家一起合作的,拍电影时,电影里(地域观)就会辐射到东南亚各地。
南都娱乐:不过你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意味着连接东南亚各国的不是语言,而是历史上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以此来构建想象的共同体连接彼此。可以这么理解吗?
陈翠梅:对,我们一起工作都是用英语,只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懂中文。这也是比较难的地方,因为当他们要建造一个东南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比较难找到一个共同的语言。欧洲的情况也是这样,欧盟他们也是会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

南都娱乐:《野蛮人入侵》和你致敬的《谍影重重》,两部电影都在探寻自我的身份,而你的电影中夹杂着很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武术,创造这么一个文化熔炉的语境,是不是加剧了主人公去探索“我是谁”的难度?
陈翠梅:马来西亚的三大民族是马来西亚人、华人和印度人。马来人可能有70%,华人可能10%左右,印度人可能10%以下。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是非常强烈的,一般在马来西亚,他们会直接说我是华人或说是中国人,会对中华文化特别骄傲。文化熔炉反而催生了非常偏激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越混杂的情况下,华人想要保留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意识)就会强化。
南都娱乐:主人公复杂的文化身份设定算是你对马来西亚社会现况的探索吗?
陈翠梅:我其实没有往这个层面做探索,可能电影里面有表现出马来西亚的复杂情况,但是老实说,这并不是马来西亚真实的样子。比如,在马来西亚,如果一个华人要跟一个男人结婚,她必须皈依回教,但在这部电影里我避开了。在这部电影里,前夫的名字故意取了一个不是穆斯林的名字,一个马来人竟然没有起一个马来人的名字,马来西亚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主角李圆满不是回教徒,如果她嫁给一个马来人就应该是回教徒。就连小孩子的名字也刻意避开,比如不能叫“宇宙”(电影中主角孩子的名字)。我没有太深入地去拍这一方面,如果牵涉到种族和宗教,那个才是真的复杂,那样的话,我就很难再去谈我自己要谈的东西了。雅丝敏·阿莫(Yasmin Ahmad)的电影常常谈宗教种族的问题,她尝试以“异性恋”来作为一个契机,讲述马来女孩跟华人男孩的爱情故事,而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华人很难接受自己的小孩变成回教徒。

南都娱乐:主人公在戏中戏时失去了记忆,同时失去了身份,然后被周围的人误以为是缅甸难民。电影中把失去身份和缅甸难民勾连起来,如此具象,这里面想透露点什么吗?
陈翠梅:我在谈论寻找自己的时候其实有几层。主角一开始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完全是被动的。接着她被导演安排被师傅磨炼,师傅打她一拳,让她才意识到那个最原始的自己——身体的本能,就是要生存下去的自己,找到对身体的控制就是认识自己的一个最原始的方法。在下一个阶段,她虽然还有身体的记忆,但是没有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当她一睁眼看到缅甸难民女孩来救她时,这个女孩跟她说话、安慰她,她就以为是跟缅甸难民一伙的。而且她在胡子杰(电影中的角色)导演的电影里面曾经演过缅甸难民,所以她会把以前演戏的经历跟现在的处境连在一起了。在现实社会里,马来西亚十多年前(可能一直到五年前),一直有难民问题。但难民问题不是从缅甸开始,我小时候住在海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有越南难民,他们来投靠马来西亚。越南难民上岸之后,他们就会烧毁船,现在海边还遗留着船烧成炭的“龙骨”。这是一段很特殊的记忆。
南都娱乐:主人公名字叫李圆满,她最后受到了宗教启迪,这个名字是否有什么特殊寓意?
陈翠梅: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我小时候看的香港武侠电视剧。我最喜欢的一部叫《越女剑》,我小时候看的那一版是李赛凤演阿青,当时我非常喜欢她。因为李赛凤的英文名字叫Moon Lee,所以我的电影主角就叫阿Moon(与“满”同音)。一个人打一百个人,这是女侠客的感觉,(Moon Lee)也是我最早的偶像。

3
马来西亚电影最大的阻力和助力是人才外流
南都娱乐:很多人称你是马来西亚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你觉得自己放在马来西亚电影中“新”在哪里?你觉得自己给马来西亚电影注入了什么?
陈翠梅:我可能在哪里都是个另类,我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不是所有人都认识我,可能有一些人被我启发。我拍的东西可能很不一样,它不是主流电影,会让一些人觉得“噢,原来可以这样子来拍电影,原来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会给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十多年前我遇到赵德胤的时候,他对我说自己会拍电影,那是因为他在2006年的大学毕业作品《白鸽》入围了釜山电影节,而那一年我的《爱情征服一切》拿了个大奖。他有看过我的电影,他觉得我用一个迷你DV,用一万欧元拍出来的东西,原来也可以拿奖。他觉得我拍得很粗糙,觉得自己也可以拍,于是,他回去缅甸拍了第一部长片《归来的人》。我当时有一个东南亚短片的计划,就找了6个东南亚华人导演,每个华人导演拍一部他们国家的华人故事,包括了赵德胤、蔡明亮、阿萨拉(泰国导演)……我拍的叫《南方来信》,讲述东南亚华人的故事。赵德胤后来跟我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投资,我是他的第一个投资人。他觉得自己拍的短片《安老衣》还可以讲下去,后面他延续这个短片拍成了《冰毒》。《冰毒》后来去了柏林电影节,那一年还代表台湾地区冲击奥斯卡。那时我才知道,哪怕我拍得不好也能给别人带来影响。

南都娱乐:马来西亚过去是香港电影很重要的海外市场,现在则是我们内地重要的海外市场,你如何评价近些年引进的中国电影?
陈翠梅:今年春节我有看《流浪地球2》,可能我在马来西亚没有经常在电影院看中国电影,我接触的中国电影是来中国参加电影节时顺带看的。在马来西亚还是好莱坞电影居多,我们的电影院就很少比较有艺术性的电影,很少会引进。我其实一直想要去看电影,但是我只来得及看《封神》。我特别想看《孤注一掷》《八角笼中》。今年的暑假档好像复苏起来了。
南都娱乐:近些年中国电影很多犯罪类型片(比如《唐人街探案》《误杀》《消失的她》《孤注一掷》)的舞台开始慢慢设置在东南亚。而在你的电影中,有一幕是主角演戏的资格被一个中国演员给取代。据你观察,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张会影响马来西亚吗?
陈翠梅:我觉得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在过去10年、20年的时间里都有发生。最开始可能不是在电影上,主要是贸易上的往来,有很多中国的投资进入马来西亚。我们马来西亚房地产的建筑基本上都是中国建筑公司做的。
马来西亚华人是挺欢迎中国人的,我们毕竟有这个情意结,马来西亚华人是特别拥抱大中华的。很多中国人会到马来西亚旅游定居。马来西亚的华人可能从十五世纪来一波,然后十八九世纪来一波,现在好像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过来,他们可能来做生意、投资,也有可能会住下来。这会儿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导致中国餐厅或者中国超市越来越多。留居在东南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这边工作居住的时候,电影肯定会有更多的东南亚题材,包括现在热议的东南亚诈骗。很多剧组来马来西亚取景还会觉得很新奇,这边拍摄电影的经费不高,所以有很多中国剧组过来,去槟城或去马来西亚海岛拍摄的都有。

南都娱乐:会不会担心这种犯罪题材的电影多了,会影响大家对马来西亚或东南亚的观感?
陈翠梅:我倒不会担心,毕竟有很多中国人居住在这里,他们知道东南亚的真实情况。马来西亚人也害怕去柬埔寨,因为我们也听说很多诈骗的故事,很像是“野蛮人入侵”,大家都觉得对方是野蛮人。我们有一阵子真的到处听到新闻说“不要去柬埔寨,很危险,会被抓进去,逃不了”。但我们毕竟有柬埔寨朋友,也知道不至于到这种情况。
南都娱乐:你认为目前马来西亚的电影市场发展最大的阻力和助力是什么?
陈翠梅:最大的阻力可能还是我们的政策,马来西亚没有太清晰的政策支持电影,导致很多人才都会外流。我们在政策上是不公平的,也没有一贯性。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会改善,目前他们至少都还在积极地跟我们电影界去谈,要去改善这个政策会花一点时间。
而助力,同样是人才外流。世界各地都有马来西亚电影人,好莱坞有,中国有,欧洲也有。如果他们把经验带回来,那对马来西亚电影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助力。马来西亚很多议题跟其他国家人不一样,我们文化还是挺复杂的,会有不一样的故事。
采写:南都记者 刘益帆 实习生 冯钰炫
图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