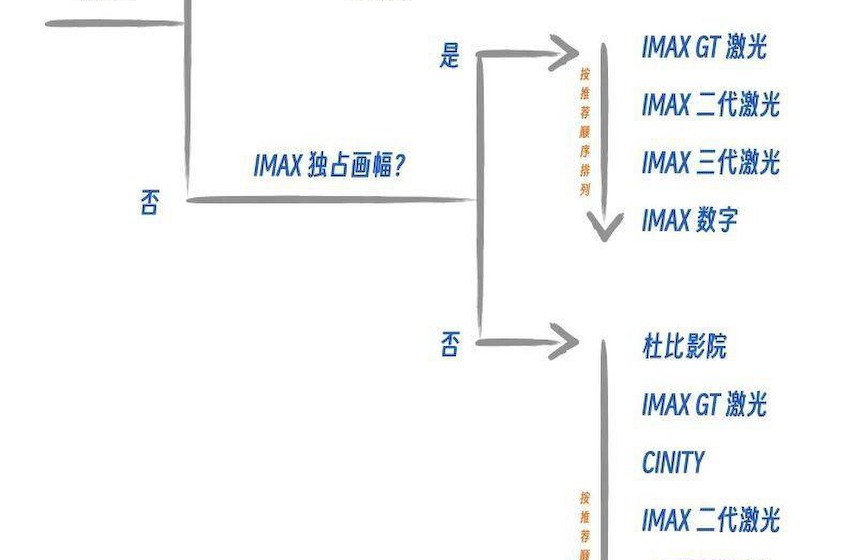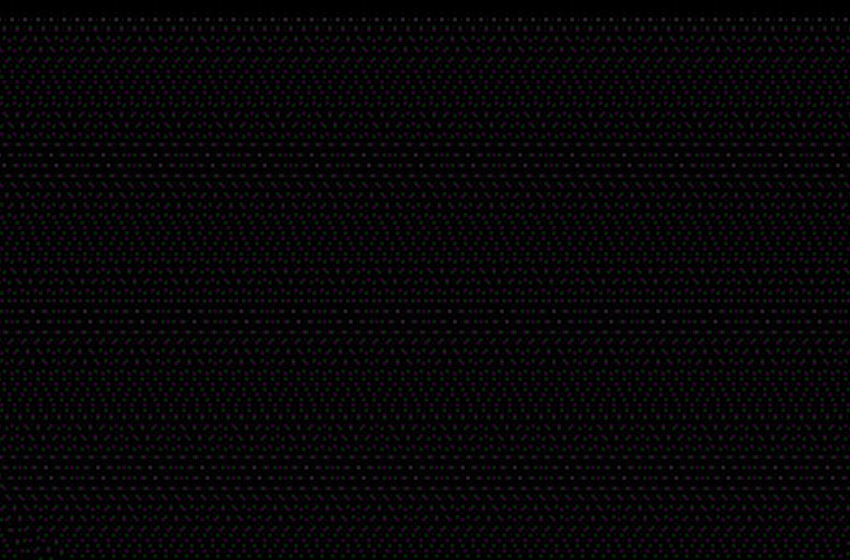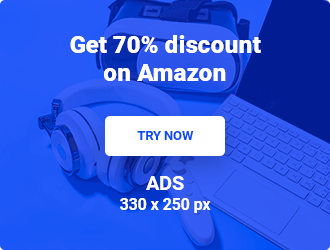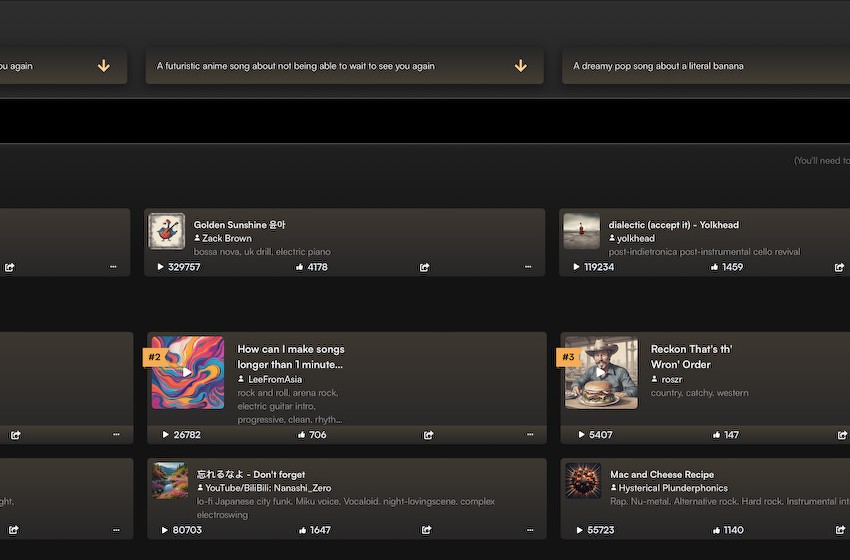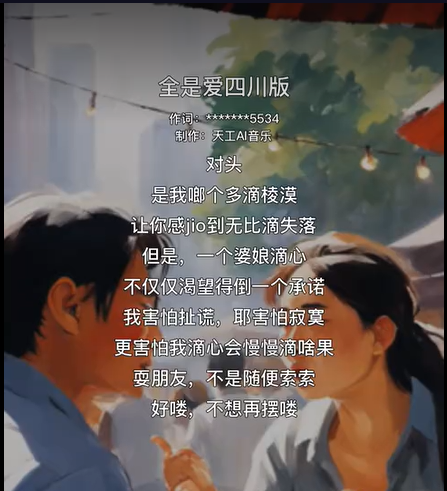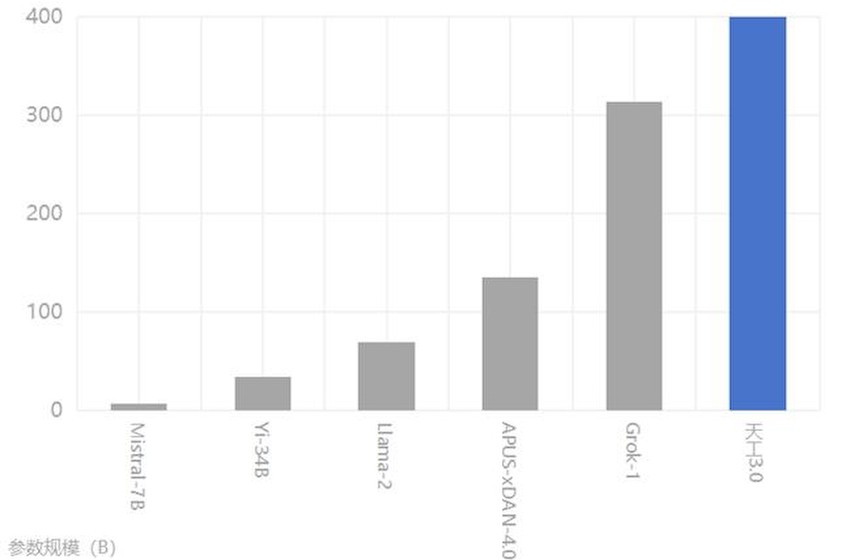论书|《天津闲人》、海河人事与《一个家族的电影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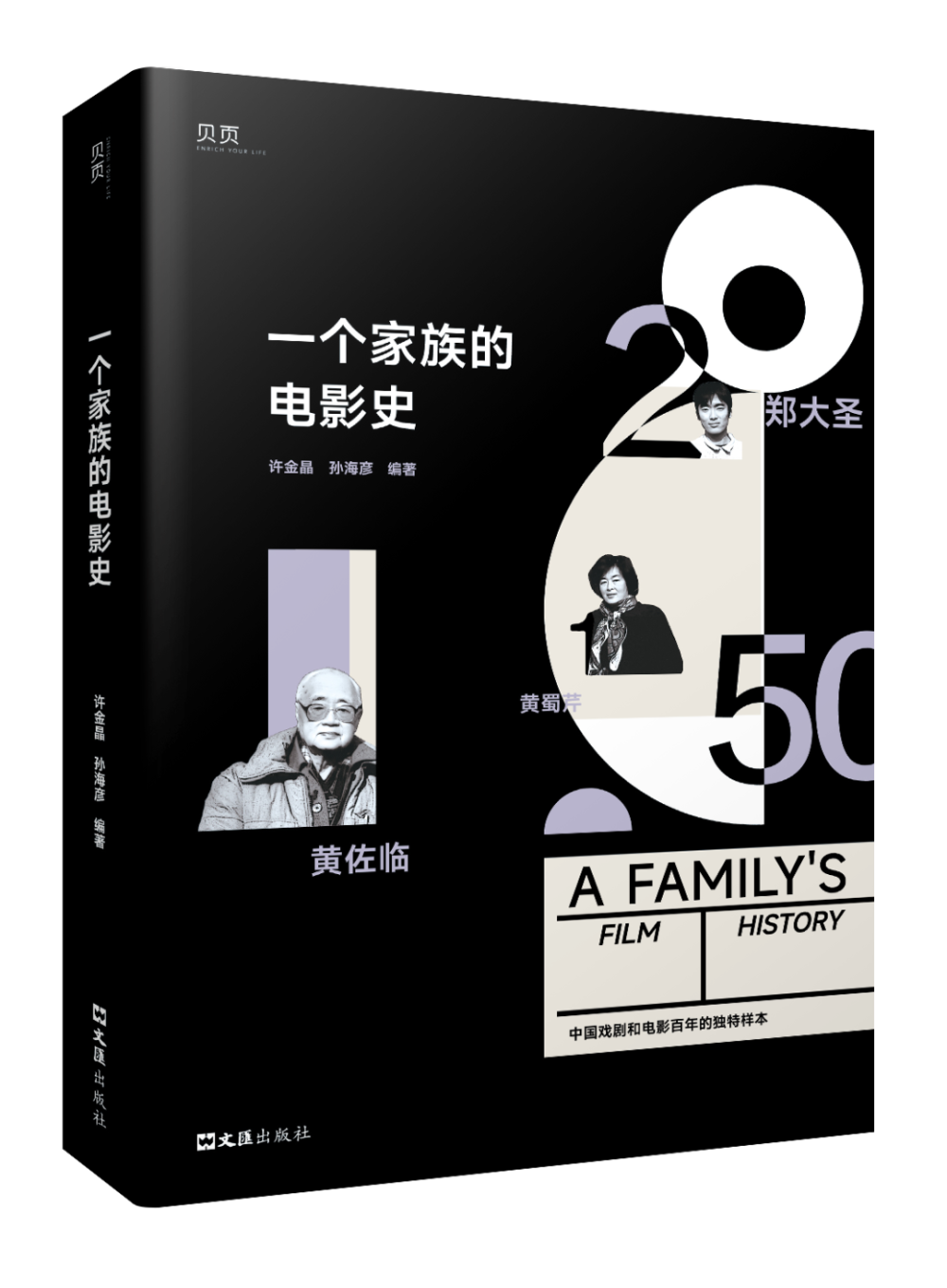
跟郑大圣所在的艺术世家结缘,源自十年前(2013年)致力于艺术电影传播与推广的“后窗放映”在南京成立时、于位于紫峰大厦的卢米埃影城(已于疫情期间关店,现址为上影紫峰影城)策划的首轮电影展映。此次展映,不只让我接触到包括万玛才旦、杨瑾、陈卓等导演的优质艺术电影作品,也经由后窗的高达介绍,催生了我对郑大圣导演做的第一次访谈、以及跟大圣之间的相识相知。
在十年前的那次展映当中,大圣是唯一一位同时展映了两部电影作品的导演,一为《天津闲人》,一为《危城》,均记录民国战乱年间的悲喜离合往事。《天津闲人》里的戏谑与黑色幽默,跟《危城》里的温婉与深情,其实都是中国延绵千年的文化根脉里的重要底色。对于自幼喜读历史的我来说,这样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符码、且有着深沉的人文历史关注的电影作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为江南时报·文艺范周刊撰稿的后窗放映成立的系列报道当中,大圣是唯一一位以专访的形式呈现的导演。多年以来,大圣一直以轻松随意的光头形象视人,然而这种“光头”,却丝毫没有带给我如京城“老炮儿”一般的油滑与江湖气息,而是一张口,就有一种深受家族血脉浸淫的云淡风轻与气定神闲。这样的气质,之于一位历史与艺术爱好者来说,是极具亲近感的。
在那次访谈与相识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会反复把《天津闲人》找出来再次观看。电影中那种融“阿Q”精神、实用主义、自嘲与自我安慰于一体的市民精神,是在所谓雅文化之外、中国城乡大地上的普通百姓度过战乱与困厄岁月的重要法宝。每次观看这部电影,也足以让我想起自己在北京读大学时、之于天津城的种种人事记忆:北航计算机系关系最好的同学——天津人孙凡时不时冒出的“挺哏儿的”的口头禅,第一次跟孙凡一起去天津、在起士林品尝的美味西餐、在海河边的开心徜徉、以及之于五大道租界老建筑的震撼与敬畏,在天津跟中学几位女同学聚会时,女同学在南开、天津外国语学院等高校里浸淫多年之后的从容与智慧,还有刚刚工作之初、跟在《新京报》一起共事的好友周扬一起同游天津时,她久居天津的知识分子父母的从容谈吐与优雅气质……记得当年读史书,曾云近代天津城,伴随着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多年来的苦心经营,颇有跟上海对应的“北方近代第一城”的美号。而从祖籍天津的大圣导演的电影《天津闲人》,到平凡如我、在生命旅程中接触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天津人形象,融开放、自信与世俗、灵活于一体的天津人与天津文化,在我的心灵世界里越发清晰。

于是就有了后来,对大圣做的一篇系统梳理其电影创作生涯的访谈,后来收录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里。为了这篇访谈,大圣给我寄来了他截止当时所有的电影作品的光碟,而这篇访谈,也是迄今为止海内外问世的唯一一篇系统梳理大圣电影创作的访谈文稿。而在本书出版之后,我对大圣电影创作的守望与观察,又在他电影创作以来最好的一部作品——《村戏》的评论与访谈中,得以延续。
有了这样的交流与信任基础,由大圣创作的记录与观察,延伸至大圣所在艺术家族的记录与观察,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那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临之初,我跟爱人小鱼都以居家办公为主。在工作之余的那些闲暇时光里,静居家中、无法外出活动的制约,让我们选择了于老电影之中、寻求心灵安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圣的外公黄佐临、母亲黄蜀芹,才从当年对大圣的报道中简单的背景话语,转化为真正进入与影响自己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作者。于是就有了为大圣家族、以口述访谈和一手文字编选的形式,策划出版一本书的设想。而这样的设想一经跟大圣提起,就得到了他的大力首肯与支持。在那些于小区之内封闭的日子里,到小区门口、取回一大包大圣寄来的家族主要代表的相关书籍和电影、戏剧作品光碟的资料,是最为难忘和美妙的记忆,没有之一。
于是,就有了对这些文字、影像资料的反复阅读、观看与笔记记录,由此形成的上万字笔记的打印文稿,至今仍然存放在我们简陋书房的写作台上。让人难忘的是,对黄佐临、黄蜀芹、郑大圣文字、影像作品的系统阅读与观看,从来就不是一种主体如我对客体如资料般的交流过程,这些虽老旧、但却依旧生动无比的文字、影像背后,我读到、看到的,是认真、勤勉而温情、浪漫、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大写之人”的形象。就以黄蜀芹导演最重要的两部电视剧——《围城》和《孽债》为例——青少年时看《围城》,纯粹就是个热闹,不甚了了,而疫情期间重看,之于知识人的人性阴暗面与局限性的种种描绘,足以让我明了所谓“象牙塔”式的乌托邦世界,从来就是并不存在的,也能对自己自少年以来的学术梦想、多少有几分释然;再说《孽债》,少年时看首播,正值自己家庭变故,看到的是满满的共鸣与共通的孤独感,而这一次重看,则会在简单的个体共鸣之外,看到导演无意间记录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街市的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信息。美国知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代表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有言,最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都应该将研究者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其研究的议题、实践与具体表达当中。由是,对《一个家族的电影史》的功课、访谈与文章编选的过程,就是与中国戏剧、电影百年发展进程中这个独特的艺术世家样本的每一位艺术家隔空心灵相伴、进而开拓与丰富自己生命世界的旅程。对于这种结缘,我无比感恩。
从黄佐临、丹尼夫妇,到黄蜀芹、郑长符夫妇,再到郑大圣、沈昳丽夫妇,这个延续三代的艺术世家,起于天津,游于英美,成于上海,而天津与上海,刚好又是中国近代以来南北两方最为开放和现代化的都市。通过这个艺术世家的成长、延续与传承的历程,也可以看出开放、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势的不可阻挡,即便在当下,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文化交流,可能面临种种逆流,我们对于天下大势,仍然应该持有起码的乐观与信心。

在本书下厂印刷、即将出版面世之前,我跟本书的共同编著者、也是相守近十年的爱人小鱼,曾经谋划好了一次久违的天津周末之行,计划探访南开、走走五大道和海河、再看看南开旁边友人运营有时的独立书店。然而因为小鱼突如其来的病患,这场天津之行,只能被迫临时取消。在医院里陪护与相守的日子里,《一个家族的电影史》悄然问世。我陪护之余重读本书,于“天津”“租界”“海河”等熟悉的关键词里,开始再次畅想我俩夭折的天津之行——生命中,总是有太多的不可预知与意外,然而于这些不确定性与风险之中,尽力把握自己能掌控的时间与能量,奋力书写,纵情拓展生命的边界与可能,不正是中国古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人生的应有之义吗?
就此搁笔。
2023年8月12日上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23年9月8日刊发于天津日报·满庭芳版,见报时有较多删改,此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