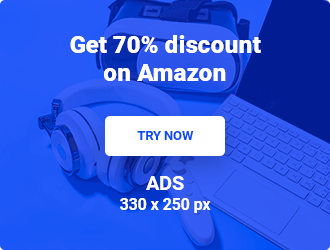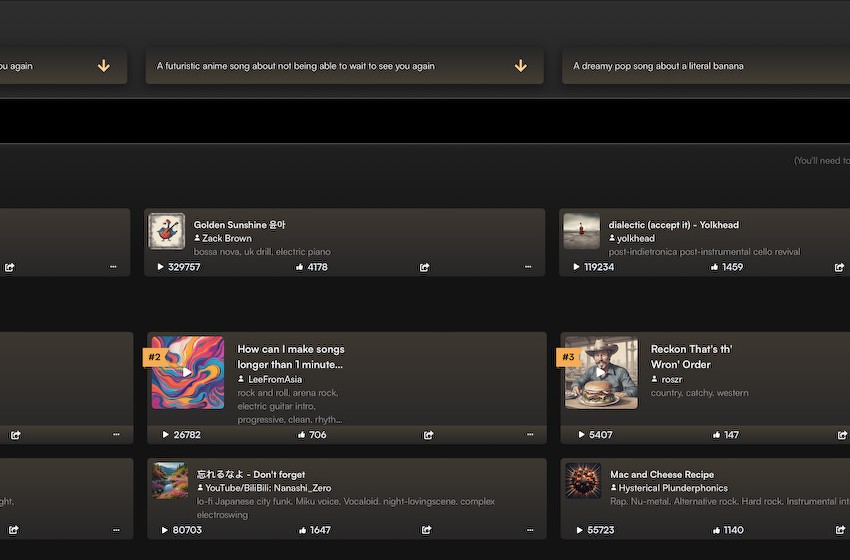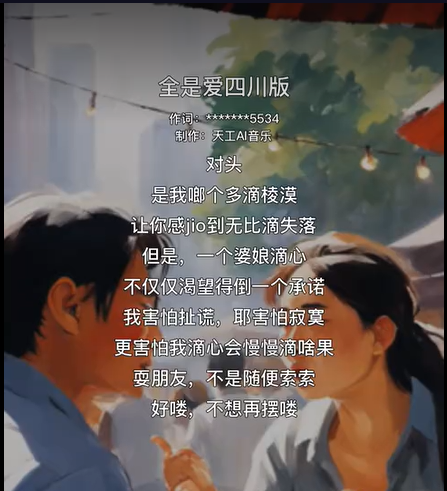“永远的外来者”:陈哲艺的十年导演之路
对于导演陈哲艺来说,《燃冬》有特殊的意义:他出生于新加坡,常年生活在伦敦,最近刚刚搬去香港,这是他第一部在中国内地拍摄的作品。
电影讲述了东北延吉相识的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在几天时间里相聚又分离的故事。影片的前半段,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法国导演特吕弗的名作《朱尔与吉姆》,认为这是一出青年男女爱情纠葛的情节剧。但随着剧情一步步深入,我们会发现主角们的故作轻松和自由背后藏着隐痛和压力。

《燃冬》讲述了三个年轻人在几天时间里相聚又分离的故事,他们的故作轻松和自由背后藏着隐痛。 (受访者供图/图)
很长时间以来,不到四十岁的陈哲艺,电影却被业内人士评价“老气”。他觉得这并非批评,而是说他有一颗“老灵魂”,作品比较成熟,让人以为是“五六十岁的人拍出来的”。有人好奇地问他:“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失控的陈哲艺是什么样的?”
“我想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区,想去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拍电影,拍一群我从来没有拍过的人,我想拍青春,想拍年轻人……”于是,《燃冬》的雏形在他心里萌生。
偶然的机会,陈哲艺有了一段空闲时间,他立马想到可以在中国最北方拍摄一部电影,在还没有剧本的情况下,他叫上制片人谢萌开启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冒险”。那是2021年,陈哲艺从伦敦飞到上海,经历了漫长的隔离,他在酒店写出剧本大纲。
首先确定了之前有过合作的周冬雨加入,接着定下刘昊然,最后是屈楚萧。他放弃了原本熟悉的拍摄方式,在开拍前十天才创作出最后的剧本,仿佛要刻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电影完成后,入围了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卖出几十个国家的版权,并很快在中国定档上映。《燃冬》选择在七夕节定档,但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上映半个月以来仅有2500多万票房,豆瓣评分6.1,均远远低于预期。

《燃冬》入围了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卖出几十个国家的版权,但在中国内地公映后,票房和口碑均低于预期。 (受访者供图/图)
陈哲艺希望观众可以看到自己的表达,但不少观众并不认可,他们批评这部电影不够真诚、根本看不懂。
2023年8月底,陈哲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自己因为恶评情绪波动非常大,仍在疗伤。“看到电影的反馈,会觉得我们真的在看同一部电影吗?……你可以说它不完美,但你不能说它不够真诚。”
“优等生”创作者
“你起步这么高,接下来蛮难的。”2013年,在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庆功宴上,李安曾对陈哲艺说。
彼时陈哲艺29岁,刚刚凭借处女作《爸妈不在家》夺得第66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和第50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击败的对手包括王家卫、贾樟柯和蔡明亮,一举成为那年华语影坛最闪耀的新星。

新加坡导演陈哲艺,出生于1984年,电影作品多次入围戛纳电影节等国际奖项,代表作有《爸妈不在家》《热带雨》等。 (受访者供图/图)
《爸妈不在家》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部入围戛纳电影节并获奖的影片,还以90万新币成为该国当年年度票房季军。这部电影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取材于陈哲艺的少年经历:主人公家乐的父母陷入各自的困境中,他反而和家里的菲佣泰莉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却浑然没有发现,自己度过青春期危机的同时,他的家庭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处女作的成熟并非偶然,在此之前,陈哲艺已经拍了超过十部短片。15岁那年,陈哲艺用积蓄购买了一台二手的摄影机,开始尝试拍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纪录片,记录了同级同学的生活,断断续续拍了一年,后来剪成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并用它申请到了电影学校。
从新加坡入读大学一直到申请英国皇家电影学院期间,陈哲艺从来没有停止过拍片的尝试,他利用自己的积蓄,申请各种基金,动员身边的朋友,想尽办法拍摄。24岁那年,他的《阿嬷》入围戛纳电影节短片主竞赛单元,隔年《雾》又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短片主竞赛单元。
渐渐地,陈哲艺发现短片再也找不到投资,他回忆:“对于新加坡的影委会等机构来说,我已经不是短片新人了,他们想支持更年轻的作者。但在国际上,仿佛也只有拍过正规长片的导演才会被认可为一个真正的导演,才会被真正纳入电影工业体系。”
十年间,陈哲艺拍了四部电影,平均两年半一部的速度对于一个正值壮年的导演来说不快不慢。但自《爸妈不在家》问世后,陈哲艺足足六年没有拍片,后三部电影是在近四年中陆续完成的。
《爸妈不在家》诞生后,片子卖去了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陈哲艺不得不用了两年时间为宣传这部电影做环球旅行。等到终于静下心来,他又要面临家庭的挑战:他和妻子在生育问题上遭遇了困境,好不容易儿子降生,生活节奏陡然不同……这段经历后来被他曲折地写进了电影《热带雨》,女主角林淑玲结婚多年没有孩子,时常需要打排卵针,却依然无法挽救婚姻;另一边,她的事业也遭遇瓶颈,作为马来西亚移民的中文老师,在新加坡中文式微的环境中无所适从。
陈哲艺觉得生活和创作是绑在一起的,他始终无法创作一个和自己无关的角色,哪怕是在英国拍摄的关于非洲难民的英语片《漂流人生》,也是他对自己十五年英国生活的总结。
谢萌曾用“优等生创作者”来形容陈哲艺,“几乎每一个步骤都很严谨”。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他一直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不论多么枯燥的课程,他的排名都是数一数二。为了打磨一个剧本,陈哲艺愿意花几年时间;和演员讲戏,他会要求对方哪只眼睛落泪……演员章宇说他“太精准了,推着演员给到想到的东西”。
陈哲艺觉得或许因为自己是80后,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不太理解年轻人所谓的“躺平”。“我完全不懂‘躺’,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也非常忙碌,我在FIRST训练营这些天,很多不是我管的事情我也会管,跟着学院修剧本、看现场、跟剪辑……半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只睡4个小时。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只能通过Vlog去了解年轻人。我现在看很多电影,年轻人被网络文化影响很深,它们已经有点不像电影,更像是‘B站+抖音’的梗。”陈哲艺有些困惑。
“
还需要我这样的导演吗?”
疫情期间,陈哲艺感到一种巨大的存在危机。2019年,《热带雨》上映,隔年就遭遇疫情,很多地方的宣发工作被迫停止。电影在法国电影院上映不到两周,欧洲也开始封控。同行朋友不少陷入失业,电影院也都关门了。“大家都开始看线上平台,在家刷短视频,还需要我这样的导演吗?”陈哲艺问自己。那段时间,妻子居家办公,陈哲艺洗衣做饭,他感觉自己失去了身份。
《燃冬》中,三位主人公也总是在寻找自己的身份,有种渴望自由而不得的焦虑,这些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感受。“我真的很想突破自己,不想一直重复。”陈哲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发现几乎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很焦虑,也都很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自我表达,他开始好奇,“我想要弄清楚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陈哲艺在社交平台上观看了很多年轻人拍摄的vlog,在B站和小红书等平台上,他观看了许多年轻人拍摄的Vlog,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已经很不一样了。 (受访者供图/图)
在陈哲艺笔下,三位主人公都是在生活中被打败的人。
周冬雨饰演的娜娜是退役的花滑运动员,原本可以进入国家队参加冬奥会,却因为腿部受伤不得不放弃梦想,她有些自暴自弃地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只身前往延吉当起了导游;
刘昊然饰演的浩丰是所谓的“小镇做题家”,从小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一家金融公司,虽然有高薪体面的工作,却患上抑郁症,逃避就医;
屈楚萧饰演的韩萧很小就辍学在家,跟随阿姨从四川来到吉林,在家里开的小饭馆里混日子,他过早地放弃了自己,不愿意再和别人竞争,甘心做一个“小镇青年”。
三人因浩丰丢失手机而结识,继而开始了几天的漫游,他们在书店偷书,在旷野骑车狂奔,在夜店偷偷流泪,在斗室寂寞相拥……陈哲艺肆意地想象青春应有的状态,最终三人登上神往很久的长白山,遇到了一头熊。就在三人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的时候,熊只是嗅了嗅娜娜受伤的脚踝——她无法面对的伤痛——就离开了,三人也决定改变现状,开启新的可能。
“这三个人在短期内有一段相处,最终他们不是谁和谁在一起,或者有一个所谓的happy ending,而是有一种很深的缘分或情谊可以在彼此心中种下什么,是可以改变你的。”有一次,陈哲艺在法国的影展接受采访,结束后他和记者一同离开办公室,一路上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不知怎么记者就告诉他很多自己的事情,从为何喜欢亚洲电影聊到自己分手的前女友。“后来我们没有再见过,但是他却和我分享了很多个人的事情,这之后他可能收获了一些释怀,我也很珍惜这种陌生人之间的交流。”
2023年7月,陈哲艺受邀担任FIRST青年电影展训练营导师,需要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帮助七个年轻剧组完成他们的短片。在影展期间,不断有电影人和他聊起艺术电影的未来,表达各自的忧虑。
他说:“我已经算挺走运了,赶上了最后一波作者电影的浪潮,在国际电影节上艺术片还可以取得不错的商业成绩。也因为这样,我从第一部电影就积累了一批国内外的观众,我反而更担心更年轻的电影人要怎么办。”
“短片的训练对我来说是必需的,我最担心很多年轻人只拍了一两部短片就觉得自己有成就了,正好这时候资方圈了一笔钱,他们突然就打算拍长片,这是不对的。”在训练营,陈哲艺是出了名的严格,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他会想尽办法说服对方,甚至会用很严厉的语气。
陈哲艺很看好中国的电影市场,阿彼察邦的《记忆》可以卖出2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创造了该片全球票房最高的纪录。但他又转念一想,如果连一位获得过戛纳金棕榈的电影作者都在融资上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艺术电影道路的艰难可想而知。
“我有时候蛮嫉妒中国年轻人的,训练营可以给你提供预算和器材的支持,市面上也有很多短片扶持的计划和长片的创投。我来自一个很小的国家,人口只有五百多万,新加坡一年的电影产量只有20部左右,疫情后降低到只有10部,这10部当中不会有任何一部艺术片。所以我在新加坡的导演朋友大多只能拍通俗喜剧,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新加坡导演必须走出国门。”陈哲艺有些感慨。
“
哪边都没有我的位置”
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是一个炎热的国家。小时候,他唯一知道的中国东北城市是哈尔滨,缘由是新加坡曾经引进过一个哈尔滨的冰雕展,参观者需要穿上厚厚的棉衣进入展区。那是他第一次对寒冷产生印象。
既然决定要在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拍一部特别的电影,陈哲艺想到了东北。他打电话给制片人谢萌,说希望可以在中国最靠北的地方拍电影。
陈哲艺是通过小红书发现延吉这个城市的,他看到网友上传的照片和视频,发现那是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中国。一半人口是朝鲜族,到处都是朝鲜文字,街道和建筑也别具特色。第一次去东北,他下了长白山就开车去往延吉,路上找了一位导游讲解,一这段旅程的经历后来都被写进了剧本里。
“延吉市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很像是一个外国城市,是一个文化混杂的地方。”他知道作为外来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无法写一个发生在东北社会内部的故事,所以故意将三位主人公设定为外来者。
陈哲艺喜欢用“永远的外来者”定义自己,他从不觉得自己属于任何一个族群和帮派。在新加坡,主要有两派导演,一派拍华语片,大多是通俗的搞笑片;一派完全“洋腔洋调”,都不怎么讲中文。
陈哲艺的奶奶是中文老师,到了他父母一代,日常已经习惯说英语。现在新加坡的中文老师基本依靠引进,以前多是马来西亚华人,近年来中国人较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每年只有十三个本科生,一半以上来自外国,“这就是新加坡华文的困境,但没有人care这个东西。”陈哲艺说,他不认为自己的焦虑是文化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更为本质的身份焦虑。
“我这样的导演其实非常尴尬,哪边都没有我的位置,还有朋友劝我不要拍《热带雨》,认为不应该过分讨论中文教育的问题。现在的新加坡已经完全是一个英语制的国家,所有的官方文件和活动都是英语的,我认识很多爷爷奶奶,为了跟孙子一辈交流,要被迫学英语。”
陈哲艺的第一语言也是英文,和父母都是用英语交流,剧本也用英文来写,但始终坚持对白使用中文。写作《燃冬》剧本的时候,陈哲艺怕拿不准中国北方人说话的语调,会求助剧组人员以确定用词。
陈哲艺很重视语音语调,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秩序化的地方,说话的口音会暴露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和受教育程度,陈哲艺对此很敏感。拍摄《燃冬》的时候,陈哲艺希望演员在特定时候使用自己原本的方言,所以娜娜和母亲打电话时说河北话,浩丰和朋友倾吐心事的时候讲河南话,而韩萧和阿姨讲四川话,出门工作时会说朝鲜语。这些既符合陈哲艺对他们“外来者”身份的定义,演员用家乡话表现也更加自然。
2021年,陈哲艺爆发式地拍了两部电影,《燃冬》之后是《漂流人生》,后者讲的也是身份认同,以一个非洲部落公主在英国的遭遇为线索。从研究生开始,他在英国生活了十五年,结婚生子、建立家庭,却始终无法完全融入。
陈哲艺的祖辈从福建南下到新加坡生活,近百年时间后,等于和家乡切断了联系。“但是我觉得唯一不会变的,就是习俗和饮食,它告诉我们自己的来处。”《燃冬》的结尾,娜娜、浩丰和韩萧告别了彼此,踏上新的旅程,娜娜终于懂得和过去和解,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去电话,告诉他们自己过年要回家。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英国人,反而保持了一个外部视角观察周围的一切,拍东西也没有负担,因为我在哪里都是外人,可以用更客观的角度看待这个地方。可能本地人看了(我的电影)之后也不认同,认为我选择的东西是不入流的,但依然觉得它很美,我想把它拍出诗意。”陈哲艺说。
为了帮助《燃冬》的宣发,陈哲艺注册了豆瓣,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开头写道:“战战兢兢地自己和自己卷了十年,拍《燃冬》让我有一种回到原点的感觉……因为疫情让很多电影院都关闭了,我对不被看到的电影、不被看到的自己,都产生了存在焦虑。是真的,这种焦虑催促我去用实践证明,我还会拍,电影还需要在那里,还会有人进影院看电影。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