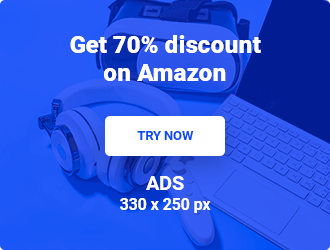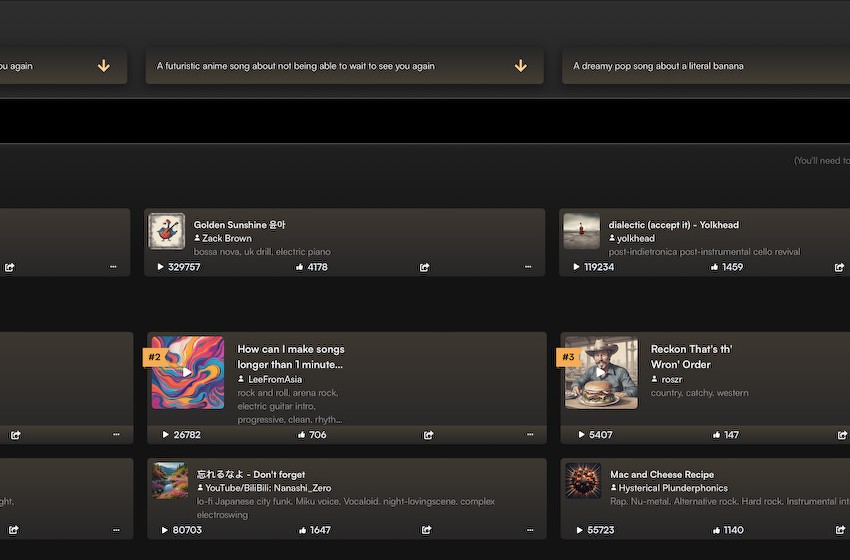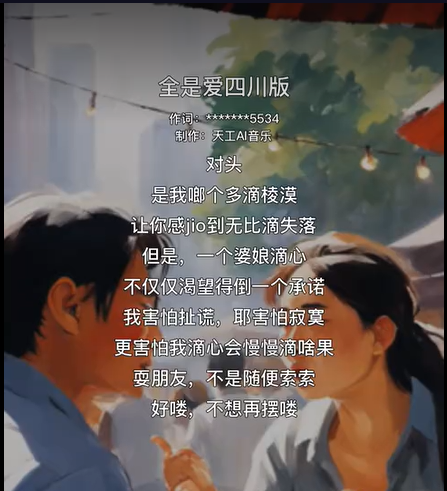《永安镇故事集》 在电影里开电影的玩笑

以又写实又促狭的视角,大开电影的玩笑,还原了剧本穷途末路的创作过程。
2021年在平遥国际影展首映、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后,时隔近两年,青年导演魏书钧的长片《永安镇故事集》于2023年9月公映。
魏书钧及《永安镇故事集》做到了两件事:第一,打破了青年导演第二部作品扑街的魔咒(2020年,其长片处女作《野马分鬃》在平遥首映,大受影迷喜爱);第二,这部电影的拍摄故事,在影迷中流传,近乎传奇。
原版《永安镇故事集》有四个小标题,讲四个带有寓言性质的故事。剧组人马到达湖南,在片场十多天后,魏书钧感觉原剧本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与合作编剧康春雷决定把原剧本推翻,又花了极短的时间重写剧本,制片人重排主创,十多天后,一部全新的电影竟然顺利如期开机。我们最终看到的是三个故事,分别用了三部国产片名:《独自等待》《看上去很美》《冥王星时刻》。
康春雷提出的第一个故事让魏书钧眼前一亮:片场食堂有个不甘于小镇生活的年轻母亲,对剧组充满好奇——这来自康春雷的观察。
魏书钧接着写了第二个故事。一个想要转型的女明星因为要拍这部戏回到家乡,受人情纠缠之苦。老同学拉她上商务饭局;青梅竹马假装偶遇,带她到家里做客,是想让她帮忙点拨家里孩子艺考。剧本问题也很大,女明星眼见着编剧春雷和导演刘洋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这就到了第三个故事,由魏书钧和康春雷共同执笔。我们看到的《冥王星时刻》里,刘洋和春雷在一个月里改剧本、推翻剧本、和各路人马打交道,身心俱疲,开机前夜,两人发生了关于创作观的不可修复的争吵。
魏书钧在采访里表示,一些生活中没有说出来的话,经过虚构创造,被放到这个故事里。影迷自然好奇,这些争吵有多少来源于电影创作者真实的工作处境。

《野马分鬃》(以下简称《野马》)算是部半自传体电影,主角左坤是录音专业学生,魏书钧也是学录音出身。到《永安镇故事集》(以下简称《永安镇》),魏书钧主动延续、回应、放大了这种现实与虚构的互文。
刘洋爱听说唱,想搞音乐,魏书钧一样。编剧春雷,就由《永安镇》的编剧康春雷饰演;春雷是不得志的文学青年,写了六年剧本,康春雷写《永安镇》的原剧本,断断续续也拖了六年。
《永安镇》首映时,观众笑声不断,大抵是因为本片、尤其是《冥王星时刻》这一部分,以又写实又促狭的视角,大开电影的玩笑,还原了剧本穷途末路的创作过程,以刘洋和春雷为圆心,对进进出出的角色无情扫射,无差别攻击。
比如制片人,代表的是讲钱但不懂艺术的人,刘洋和春雷默契地站在同一阵营与之对抗。比如影评人吴老师到片场探班,在船上品茶,刘洋态度和气地陪着,春雷只有站一旁划船的份儿。这个吴老师讲话自以为权威,评价电影动辄上升到以后要写进电影史、所以该当如何的高度,一股端着的“爹味”,把对电影的批评看成了自己的权力,实际上言之无物,让我想起不少现实中的“影评人”(甚至在平遥电影宫排队等候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就看到类似的人,讲类似的话)。
但这样的嘲讽并不会让人感觉油腻,因为炮火也面向导演和编剧自身。
刘洋想把电影从四个故事砍成三部曲(这一点也与现实情况呼应),拉下脸劝制片人,为了华语电影勇敢一次——“为了华语电影”这样自恋的大词实在让人厌烦。
过了蜜月期,刘洋和春雷组成的小共同体产生裂隙,刘洋嫌弃春雷,说剧本只是半成品。春雷自我实现的热情被浇灭,在忙于应付导演需求后越发疲惫,听完导演大讲对真实的追求,说,那你怎么不拍纪录片呢?春雷去和美术指导抱怨刘洋,美指油滑,两不得罪,持中不语。
《野马》中的左坤就处于这种不太得劲的人际关系中,他见过一点外面的世界,课上不专心听讲,嫌老师讲的脱离实际;跟着拍电影,他冷眼瞧导演吹捧摄影师,笑称后者晒出了“坎城的肤色”(指电影入围了戛纳某单元),但他看不上的那些人好像是成功者。
《永安镇》的刘洋和春雷处在这个权力系统里,对外界也是有点不屑,又不得志。片子开机在即,焦头烂额时,刘洋还要选,开机时鞭炮要放多少响。在开机前夜,刘洋和春雷闹翻,刘洋把剧本一扔,暴怒,你就给我这么一坨?
就用这么一坨,电影真的开机了。鞭炮声里,剧组拍大合影。关于电影,导演用一整部电影的时间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由于没有机缘看魏书钧那部可能失败的作品《浮世千》(在采访中,魏书钧谈到,那时他还不懂怎么做导演,片场甚至有他没他没区别),只能以目前的一短二长三部片子(均入围戛纳不同单元)来了解他的表达。
短片《延边少年》里,少年花东星想要离开乡村,找父亲要旅费却不太顺利。《野马》里,左坤开着吉普想去草原,但没毕业,车也坏了,驾照吊销,和哥们儿把卖不出去的CD当飞盘扔。回头想上述作品里可咂摸的段落,都有困在原地的怅惘,我记得《野马》最后的台词:我们难道不能重新出发吗?我们是时间的主人,命运的主宰,灵魂的舵手,对吗?
可日子还是得浑不吝地过下去。
《永安镇》里,不论是小镇女人还是剧组成员,本也身处困局难以挣脱,但首映看过片子两年后,我记忆里闪光的情节、台词,大都是关于华语电影和青年创作者的“段子”。讲一部电影差点拍不出来——这带来的嘲讽、欢乐,好像喧宾夺主,盖过了可能有的更恒久的内核,我不知是好是坏。